植根于大地的写作
 韩少功
韩少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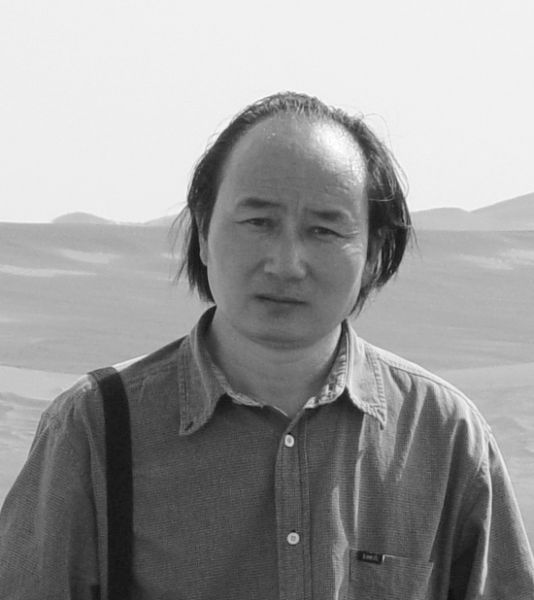 刘亮程
刘亮程阎晶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和他的创作真正能够结合起来,别人也能从中得到启示,这是今天座谈的主要议题和目的。如今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仍然不少,他们或是根据自己的童年记忆、电视报纸的听闻,或是亲身走上三五天的采风等各类方式得出一些结论,写下一些作品。可我觉得这远远不够。你们二位,韩少功长期生活居住在乡间,刘亮程就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作家,因此在这方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刘亮程:我十分欣赏少功老师的这种生活。他很早就创建了自己的写作模式,正当事业的高峰期,悄然隐退,回乡务农,把自己还给生活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很多作家最终都没法把自己还给生活,他们被固定到某一种岗位上,选择自己不想过但又迫不得已去过的一种生活。归乡13年了,少功选择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放下的方式。当时我听说他的这个决定时心里很羡慕,我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一直没有真正地去工作过,只是一个闲人,总是游离于乡村和城市之间。但少功是完全放下了,谈谈你的这种放下的生活吧。
韩少功:当时就是有一种危机感。我发觉自己的写作开始有些勉强,不再是那种喷涌而出的状态。用我原来的比喻说,真正的写作就像谈恋爱。它自然而然地来,毫不费力,滔滔不绝。而职业化的写作,勉强去写就像三陪,虚情假意,挤眉弄眼,非得要写成什么,好去赚它一笔。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个问题已很严重,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但我与亮程所选择的方式有些区别。我的选择是农耕式的,待在一个地方,守住一亩三分地,埋头苦刨。而他是属于游牧式的,格局和眼界较宽,从现实到远古,从汉族到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在不停地发散,像牧人一样不断拓展新的牧区。
南方的天很小,山很多,它不是那种大天大地。南方的乡村就好比在山洞中,人口稀少,里面定居是几十代不变的那群人,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积淀下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是生活在如今这个社会现实之下,最底层的,自认为是最卑贱的下等人。和他们相处,比我在文人圈、知识圈里面得到的信息多得多。与同业者打交道,你读的那几本书我也读过,你所说的那几条微博我也知道,因此这种交流效率低,信息差异较小。当然,对走出圈外的交流,你也不能太功利。如果仅仅是为了写一部小说去采访他们,那样做效果也不见得很好,实际上也不如你的期望那么高。事实上,惟有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共处才能给你滋养,回头看,不经意的收获往往是最好的收获。
阎晶明:当时的您是想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创作的角度考虑才做出这个选择?
韩少功:兼而有之吧。作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作家。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能把生活变成写作的一部分。在城市中过了30多年,生活有点单调。我记得尼采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要想使你的生命变得长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要使生命处于轻度的危险中”。这就是说你要有一种轻度的压力,适度的陌生感和适度的冒险感。改革开放后,我们都是受益者。在城市中大多数人都已住上三室两厅,四室一厅,享受舒适的生活。生活环境也是全球化格局下的标准模式。沙发,全世界的沙发都这样;浴缸,全世界的浴缸也差不到哪儿去。这样一来,生活本身的差异性会流失很多。而且随着舒适度的增加,对于生活的记忆也会变少。日子突然变得很短,一眨眼又是一年了。其实不是时间太快,是我们脑子里留下的东西少了。对于作家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当时的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或是野心,说要跑到世界某个特别危险的地方,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去冒险,这也不大可能。所以我想至少要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打破生活旧的格局,比方说恢复体力劳动。我觉得长期地离开体力劳动,离开自然是十分病态的事情。对城市人来说,自然就是阳台上的几盆花。这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常态化的现象,它只是几百年间发生的一个特殊情况。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同质化的圈子里,所接触者都是教授、评论家、记者一类,也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我去的是湖南汨罗县,是我当知青的地方。我曾在那里当了6年知青,在县城又干了4年,总共10年的时间。我在那里最有利的条件是我懂当地方言。南方不同于北方,方言五花八门,更难懂。如果你连当地人说什么都不懂,没有两三年的工夫你根本进入不了他们的圈子,他们生活中最核心的层面。一旦你过了语言这一关,他们可以和你开玩笑,相互之间不需要过分的客气,有时候我甚至还可以骂他们,管管他们的私事,真正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种状态不能说给了我多少帮助,但它至少恢复了我对生活的感觉,让我增进了不少知识,加深了对其他阶层人的了解,对他们的思维意识、文化传统、审美趣味常常会有新的惊讶。在同质化的圈子里这种惊讶感很少。虽然大家在一起会斗斗嘴,开开心,但你不会惊讶。
阎晶明:您去到那里时《马桥词典》已经出版了。这本书的特点是用一种故事的语言对乡村的生活方式、方言、历史、伦理关系等方面的细节化阐释。当您再次回到乡村时,您是想试图去寻找更新的东西,还是您认为这里面仍有您认识不到的东西?
韩少功:我倒没有具体的规划和设计,只是觉得换一种生活方式,至少在两个维度都会有收获。一个是社会维度,一个是个人维度。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改变肯定会为你的个人命运增添新的色彩,就好比一棵草,从一块水土移植到另一块水土,肯定会长得不一样。在社会维度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关心社会、关心他人生存方式的人,你会有很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对底层社会的发现。但是这两种新的体验到底会结出怎样的果子,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实上,像我今年所写的长篇,就和方言没有什么关系,和地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阎晶明:您说的是您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么?它和你目前的生活状态有什么关系?
韩少功: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一定是直接的关系。生活给了我很多启发,用最常用的词来说,就是给我充电、补血、提供资源。在另一些我不知觉的方面,比如说心态的调整,也可能有影响。我家出门就是山,有时候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也许会疑问,这个世界需要文学吗?如果我还要写作,那么写作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你会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质疑自己,以此来调整自己的某些观念和心态。你会觉得文坛很遥远,某些社会事件很遥远,曾经重要的一些东西突然变得不太重要,于是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面对生活的另一面,比如关于天关于地的问题也会浮现出来。
有人说我是农民,我说那可不对,我顶多算是一个“伪农民”。劳动对我来说是享受,而非负担。劳动的过程是主动的,愉快的,不受强迫的。当然也有辛苦的时候。山区的公共服务系统比较脆弱,一场大雨就可能损毁道路,还有电力、电话、电视的网线,好几天里你如同退回到古代,生活上很麻烦。乡下虫子多呀,下雨天要排涝,晴天要抗旱等。我们想种些蔬菜,又不愿打农药,只有戴着老花镜去捉虫子。到下雨天就不能出去下地了,时间可以用来读书写作。在乡下你才理解古代文人所说的“晴耕雨读”的境界。其实,也有不少作家在乡下生活过。还有一些画家也会选择去乡下。这可能与文学和美术的个体化生产方式有关,而戏剧、舞蹈、电视等方面的生产似乎就不行了。作家们的采风、挂职也可以下乡,当然也有作用。但说实话,采风基本上是旅游,是农家乐,太皮毛化了。挂职也大多是形象工程。以前我在湖南和海南都挂过职,但戳在那个官位上,你很少能听到真话和实情,别人把你当领导,只是简单汇报,大凡都是一些数据。当然,我不是反对采风和挂职,这些也是可以的,聊胜于无吧。但以这种方式介入生活,其力度肯定会比亮程要小得多。像亮程这种工作室,就我这几天观察的来看,它既不是政府部门,也不是社会团体或商业机构,有体制的弹性,便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交往。亮程到哪里都有朋友,与民众都走得很近。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错的状态。
阎晶明:文学和生活确实是不可分割的。很多作家处于生活的夹层当中,他们对社会大众的心态、矛盾不了解,包括对自然、历史,就像您说的那样,都处于不清晰的状态,大量的信息把作家的思维切碎了。在新疆,像刘亮程这样的作家的成长过程既特殊又有代表性。他的特殊在于现在的“60后”作家大多是科班出身,大学中文系毕业便成为专业作家。而他纯粹是草根作家。而且我发现,在新疆有很多像刘亮程这样的作家,虽没有取得像他这样的成就,但成长路径大抵相同。
韩少功:历史上,优秀的作家其实大部分是业余向专业过渡的模式,比如20世纪大家耳熟能详的契诃夫、海明威,以及中国的鲁迅等。现在的问题之一正好就是业余作家的消失和难产。一个是生存竞争,一个是流行文化,把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打劫了。优秀业余作家的脱颖而出越来越难。如今北上广这些地方,从业者忙得像机器一样,没有读书的时间。每天工作8小时,而且路途上来回奔波还得三四个小时,总共十几个小时,使他们疲于奔命,与文化的惟一勾连,差不多就是地铁或者公交车上每人手里的一部手机,看看微博什么的。想想我们的年轻时代,虽然生活很苦,但晚上借一盏煤油灯微弱的光,也依然把书读得津津有味,抄得兴致勃勃,在现在看来有点近乎奢侈。在另一方面,现在的写作生产开始呈现精英化、都市化、职业化。硕士和博士满地走,从大学出来直接进入文化的要害部门,成为职业化的生产主力,操控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业余作家是从工人、农民、医生、海盗经历中慢慢成长出来的,是漫长怀胎后的分娩,而现在的很多职业写手是直接克隆,是缺乏母血的速成高产,是山寨化的大跃进。有一次,一个孩子拿一个U盘,说韩老师请您看看我的作品。我以为是散文或短篇小说,打开一看竟然是7个长篇。有一个是写明朝的,有一个是写唐朝的,有一个是写火星人的。我问他怎么写那么多,他说我们同学写这么多的很多呀,不止我一个。想想也不奇怪,他们这些在电脑屏幕前长大的人,所有关于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知识皆从电脑上来,写作便成了一种完全技术化的面壁虚构。但我们的商业体制正在鼓励这种东西,正在用这种东西训练读者,杂志一发可能就是几十万份。低体验的写作,与低体验的阅读,正在互相造就和互相繁殖,形成一种机制,一种利润可观的产业。这是一个新时代带来的新现象,我们绕不过去的现实。总之,现在一些专家在抱怨民众不读书,但反过来想,文学本身是不是也有问题?为什么文学不再有那种鲜活的能量,不再有吸引民众的魅力?这个缺钙和缺血的问题,该如何去破解?
阎晶明:是不是请刘亮程说说自己的想法。
刘亮程:有记者问我在新疆写作和在其他地方写作有什么不同。我没在其他地方生活过,但我想无论在哪儿,生活提供给一个作家的资源都足够他去写了,不见得非要住在新疆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新疆确实给人提供了不一样的环境。它的干燥、辽阔、偏远、地广人稀,以及多民族的文化生活背景,又都显得它与别处不同。新疆是一个末梢地区,它离汉文化远,离其他文化更远,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到达这个地方都变弱了。相反自然的势力更大。在这片土地上你更能感受到天地带给你的东西,草木风雨带给你的东西,这些反而能被一个人更真切地感受到。
新疆的特殊环境更容易野生出一些作家。10多年前李娟出现时我曾用了一个词“野生”。当时的李娟十六七岁,小女孩刚从山里出来,也不敢正眼看人,拿着写在方格作业本上的稿子来《西部》编辑部投稿。我正好编散文,一看就说散文写得很好呀,同事看了也说好,又怀疑这么个小女孩怎么写出如此成熟的东西,是不是抄的。我说绝对不是抄的,她找谁抄去,中国文学中没有这种东西供她去抄。这种东西只能是野生出来的,你看看李娟的生活,她随着母亲跟随阿尔泰山区的哈萨克族人四季转场,哈萨克人转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驻足,帐篷支在那儿卖一些哈萨克人日常生活所用的百货。就是那样的生活,李娟度过了她的整个青春期。走过一个又一个山沟,踩着牛羊脚印,找到一个又一个哈萨克人的毡房,把东西卖给他们。她在寂寞的成长中单独地感受了一种生活,单独地想了一些事情。然后用文字单独地呈现出来。
看新疆作家的作品都有一种单独的感觉。仿佛作家被单独地放在地老天荒中去独立面对整个自然与人世。有“孤悬”的意味。《一个人的村庄》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我写了一个在天地间无所事事的闲人。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是因为我的童年太忙了。我从很小就开始干活,还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开始打柴,割草,喂猪,家里编织的活儿都是我干。编筐、织毛衣,还做皮匠木匠活。 从我童年到青年,我们家搬过四五次家。盖房子,一个房子一盖就是一个夏天,整个过程我都在劳动。忙忙碌碌,没有闲下来过。一个忙坏了的人,选择写了一个闲人,不干活的人,一个整天背着手在村前村后闲逛的人。《一个人的村庄》写的就是一个闲人。他从繁忙的大地上抬起头来,从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中直起腰来,看天上的事,看草木的事,关心一阵风的事。
《一个人的村庄》里的主人公刘二,每天最大的两件事就是早晨迎接太阳升起,他认为此时此刻天地间最大的事就是太阳升起来了,而不是你醒了开始做饭劳动。太阳出来这么大的事没人关心,你想太阳不出来你能干活吗,人们都是大事不关心,小事瞎忙活。于是刘二代表全村人站在村东边,微笑地迎接太阳出来,然后,太阳一升上天,他就不管了,开始背着手在村子里闲转。等到下午,他又代表全村人目送太阳落下。他认为这一天下来天地间最重要的事是落日,那么大的一件事发生了村里没人管,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别人不管的事情,他要管。所以说《一个人的村庄》里的闲人是闲到极致了。刘二到人家门口,从来不推门,而是等风把院门刮开,他进去后风又把门关上。闲人不动手,动手非闲人。在村里刘二也是顺风走路,没风就不走动。刮西风时朝东走,西风停了等风向转换时再回来,要是风向不转就在东边待着呗,反正没事干。《一个人的村庄》写了一个彻底的闲人,他和村子里的春种秋收没有关系。无论是文学中还是现实中的农民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从未闲过。我想一村子的忙人总该养得起一个闲人吧,我就要当这个闲人。不然人类的忙忙碌碌有何用。这本书写了一个闲到底的人,也算圆了我的闲人梦。
《一个人的村庄》是在乌鲁木齐写的,那时我在报社打工当编辑,这本书写了近10年,后来变成一个专业作家,算是真的闲下来了。几年闲着闲着,老觉得自己跟生活没有关系了。后来就开始做一些文化项目,也是不断地在下面走、看,看到一些地方文化建设一塌糊涂。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广场上就造了一片帆,离海最远的城市到处都是帆。我们从几年前开始着手研究地方文化,介入地方文化建设,小有成就。我们做了“和文化论坛”,希望为新疆文化治疆提供一个新思路。
新疆很干燥。对一个作家,气候有时候起作用。不知你发现没有,新疆作家身上都有一种干燥的气质。大家到新疆来,都喜欢带点干货回去。葡萄干、杏干、巴丹木。新疆文学也是干货。从周涛的散文,董立勃的小说,新疆诗人的诗歌,你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干爽。新疆的民间语言方格也是干燥的。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的灵魂是干燥的,干燥的灵魂是好的。” 我的思维和语言肯定受新疆环境的影响。不知不觉中你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些都容易形成一个作家的语言方式和看事物的视觉。我记得我写《凿空》,在库车待了好长时间。一年去好几次。我和维族人在一块聊天,彻夜喝酒。前半夜我不懂维语,后半夜我说的全是维语。第二天早晨又全忘了。那样的生活要一直延续下去,我完全可以听懂他们说话。但听懂仅仅是一个方面,仅仅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不够的。更多的生活是可以看懂的,或者靠鼻子也可以嗅懂,甚至我是一个瞎子的话靠听觉触觉我也能懂。生活不只有语言交流一条路径。我记得刚开始在库车游走时,我随行带着一个翻译。后来我一个人在那里走。我觉得不需要翻译了。碰到一个老大爷,我走到他身边递支烟,他对我笑笑。不用说什么话,就像坐在自己老父亲身边,他的今生今世全在我的脑海中。他布满皱纹的脸,那样的苦笑,那样看你,或者你看他的眼神,有什么啊。
韩少功:就像谈恋爱。一个眼神就行,表白是次要的方式。
刘亮程:对。在生活中走走看看,你会觉得你已经在其中生活了多少年多少代了。没有一点是你不懂的,它和你全无隔膜。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它和你父辈的生活,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村里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我写的只是人间某个角落的生活,没有民族之分。我曾说过一句大话,即使我离开人间100年再回来,我依然能懂得大地上的事情。我能看懂春种秋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的痛苦和快乐,看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听得懂风声,鸟叫。知道风从哪儿刮起,在哪儿停住。我知道村子里一年刮几场西风,东风下雨还是西风下雨。老人都知道,但很多作家不知道。我发现好多人一打开电视就看国际新闻,不看国内新闻,不看他身边的新闻。看那些远在天边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事,家乡那么多事他不了解。懂得家乡的知识,懂得家乡的学问是最重要的。好多作家恰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把家乡架空了,去体验别处的生活,别处的情感。按照别处的思维遥远地想象人们的生活。
我觉得新疆的各民族经典对我的滋养很重要。20多岁时我也不屑于看新疆的东西,光知道我国有两大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在新疆,但不去看。那个年代我们都忙着读翻译文学,来不及看脚下的事。30岁以后我开始慢慢读新疆的东西,其他语种的东西。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11世纪左右,发生在新疆喀喇汗王朝和于阗国长达100年的宗教战争的小说。写那样一本书,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了解是很困难的,我们汉史中对那段的记载是空白的。其他的文史资料也是片段的。怎样去了解这段历史,于是我读到了《突厥语大词典》。多年前这本书翻译过来时我就读过一遍,觉得写得非常好。所以在着手写长篇时,我认真重读,一个词一个词地看。通过这本书我看懂了那个年代。
去年我给喀什师大的维吾尔族教师讲课,我说我来到了《突厥语大辞典》的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喀什噶里的故乡,走在他曾经走过的土路上,呼吸他曾经呼吸过的空气,眼见他所描述过的这些生活,就像碰到了一个老熟人一样。我跟这个地方是息息相通的。当我读懂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时我已经跟这个城市有了联系,我若是读不懂它,哪怕是在这里生活百年依然和它毫无瓜葛。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的气息和它是连接的相通的,我看到这个地方的现实,通过历史的学习,把我的情感和祖先衔接在一块。
在新疆来回走,写作,做文化,一晃就已是这么多年。像少功老师所说,这也是一个从内心世界走向新疆现实的过程。一个人的村庄是个人的乌有之乡,但随着在新疆的游走和观察,不知不觉中与一个地方的现实相遇。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游离在生活之外,做一个旁观者,一个审视者。可当我开始写《凿空》时,现实扑面而来,你躲不过去,你必须面对它的现实去说话。
阎晶明:在《一个人的村庄》里,你从一个闲人的角度去描述你的体验,你的生活。在文学上它创造了一种风格,读者在新奇的同时也深感震撼。但现在你说要把心放在更大视野之上,放眼全疆,这种思想认识无疑是更广阔了。这在你的创作上是否会产生转型?
刘亮程: 讲一下长篇小说《虚土》。写它时我40多岁,正值人生的迷茫期,不知道40岁之后是怎样。我写的是个人的惶恐感和个人的虚无感、孤悬感。写了一个5岁的孩子,在一个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一个村庄全部的生活,看见那些15岁的人在过着他的少年,25岁的人过着他的青年,4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6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甚至出生和死亡都被别人过掉了。 那部小说没有过多的故事,全是微细节。
原本我是想借《虚土》写出我们家的移民历史。在荒天野地里建造一个新的村庄。可后来我对这么写没兴趣,所以就从一个早晨开始,从一个5岁的孩子写起。移民背景也隐隐约约地穿插在故事里。《虚土》写了一个人的百年花开,他的一生在一个早晨完全盛开。这样写着,我发现早年诗歌的感觉又回来了。把从前没过完的诗瘾又续上了。《虚土》是我个人的一部长诗。
阎晶明:你提出的牧游文化,是你的文化抱负的展现吗?你想做的这个项目最后想实现什么目的呢?
刘亮程:先从游牧说起吧。我们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纠结。 在盛唐诗歌里,李白即游牧精神的代表。李白出生在西域,他拥有一种与农耕文化截然不同的情怀。而那个时期的杜甫和他是不同的,杜甫则代表着农耕精神。曾经盛开过的游牧文明在逐渐往边疆退缩。但像李娟的作品,恰好表现了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游牧精神。这是我们的游牧民族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都不一样。李娟的文字里有一种简单的快乐。李娟书写的是她在阿勒泰地区和牧民们过的一种非常艰辛和简单的生活,一年挣不了多少钱,每天坐在商店里等待哈萨克人来买东西。一到晚上,尤其是冬天,房子四处透风,要忙着补漏洞。炉子一灭,房子就成了冰窖。那样的生活要让另一个作家去写很可能就成诉苦了,但李娟一句抱怨也没有,全是快乐。她写她妹妹的恋爱。小女孩寂寞地长到18岁,寂寞地有了一场恋爱。又像一场风一样过去,没有果实。包括李娟自己,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一个人待在大山里,一个女孩的青春就这样被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被那些骑马的人过来过去看见。没有爱情。但她充满快乐。她从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获得了快乐,一种和我们不一样的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就是游牧精神。它在游牧民族的作家中时有出现,但因为语言传播途经的问题不被我们看见。新疆有一个哈萨克族作家朱马拜·比拉勒,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他的文章里就有游牧精神。《天涯》杂志刊载过他的文章,我推荐过几篇。但这样的东西让内地的读者阅读是有障碍的,它和我们的生活有隔膜感,它太远。像李娟这样的作家也是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把她的文章带到了更多的读者面前。 哪怕现在,你也不能说李娟的文字完全被人接受了。它的销量依然有限,只有几万本。
阎晶明:谈谈你的“牧游”是如何构想的?
刘亮程:所谓“牧游”就是把游牧倒过来读,有一种对游牧文明回望和挽留的意味。我们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都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所纠结,只是农耕文明最终成为主导,游牧退缩到边疆山区。我们提出了“牧游”的观念,把所有的牧业文化变成一种旅游资源。新疆每一个山沟、牧场都是好景区,游客都可以去,而这些地方没有变成景区,没有被拦起来收门票,但却是那样的吸引人,有牧民在生活,有羊群在游走,有白云,有毡房。新疆现有的景区,牧民和景区的冲突每年都有,再怎么补助牧民始终觉得不满意,你把人家的牧场直接圈起来收费,又不充分考虑牧民利益,人家当然不愿意。而我们创始的牧游是没有门票的旅游,政府出点资把牧民培训好,让每条山沟都变成景区。
牧游的最大意义是促进族群之间的交往。通过牧游,把内地游客导入到牧民家。牧游是到牧民家过日子的旅游。是走亲戚式的旅游。去深刻地体验在中国大地上还有游牧族群在生活,惟有这样,你才能知道中国不光是汉人的,它同时也是放牧的哈萨克人和打馕的维吾尔族人,是四季游牧的蒙古族等诸多民族的。这才是完整的中国。
韩少功:原来我们认为农业很落后,牧业更落后。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观念,就是阶梯式的把牧业农业化,再把农业工业化。其实,这种想法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已遇到很大的障碍。联合国最近把食品质量和安全列为人类五大危险之一。现在我们反过来想,也许原来的农牧工协调比例其实是正确的,它有利于人类的食品安全和生存质量。世界上眼下的趋势,是农牧产品价格在不断上升,工业品价格在不断下降。人类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农牧业的真正价值,包括经济价值之外的精神文化价值。
相关阅读:
- ·赵本夫:大地才是一切生命的依托(2012-08-22)
- ·韩石山:批评靠的是良知良能(2012-08-15)
- ·陈忠实:文学是我的幸与不幸 (2012-09-21)
- ·阎连科:我的写作与我的倔犟(2013-10-15)
- ·蔡志忠:更可怕的是思维僵化(2013-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