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要为文学创造思想——文艺理论家钱中文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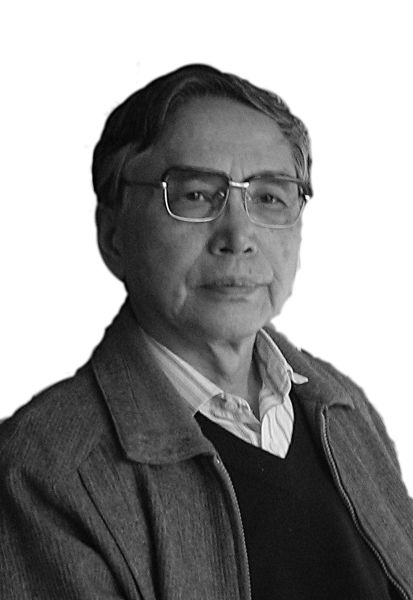
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溢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
丁国旗:您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新时期之后,因此,我想就从20世纪80年代初说起。那时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想纷纷被介绍到国内,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当时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钱中文:外国的各种文艺思想被大量地译介到中国,我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外国文艺思想进入中国之后,当时就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西方文艺思想特别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大量输入,使人感到十分新鲜。但是一些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者,往往被现代主义文艺思想所吸引,对现实主义采取了排挤甚至嘲弄谩骂的态度,染上了爱因斯坦批评现代主义者无度张扬自己的主张时所说的那种“势利俗气”。我对现代主义作品并不反感,觉得陌生新奇,后来在巴黎观看了好些荒诞派戏剧的演出,使我深为震撼,觉得其中的优秀之作,真如诉述人的命运的悲怆交响曲,但对它的宣传者的理论观点则不以为然。比如,说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落后,只是模仿,不具有主观创造精神,今后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现实主义将被现代主义文学所替代,等等。实际上,现实创作情况并非如此。于是,我就花了不少力气探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理论,并对它们各自的诗学原则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从而提出一个观点:文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文学替代另一种文学。文学史上不是现实主义文学替代浪漫主义文学,也不是现代主义文学替代现实主义文学;更迭的是文学思潮,而文学创作原则是难以更迭的,文学创作原则一旦形成,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作为创作原则,现实主义并不会被现代主义所替代,相反它可以在不断地创新与综合中更好地丰富自己。
丁国旗: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提出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问题,这一观点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钱中文:20世纪80年代初,文论界对过去的文学基本原理、文学概论颇有微词,这时文学所理论室获得了一个国家项目,要撰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合新时期需要的《文学概论》,我也参与其中。大家商量的结果是,不能重复过去编写的同类书籍,要有超越,为此先要了解中国已有的几十种文学理论书籍的问题所在,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理论的最新成果。于是我去北京的几个图书馆多次,找到了美国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77年版,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末),后来得知此书在国外已经流行多年,还有苏联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年版),荷兰佛克马与易布思合著的《20世纪文学理论》(1977版)以及美国、英国、法国作家论文学的俄译本,这些著作对我很有启发。这样,在我的提议下,作为《文学概论》的副产品,我们以“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为名,组织翻译了多种外国文学理论著作,以扩大国内学者的视界。由王春元与我任丛书主编,后来丛书加入了不少外国美学、文学理论著作,共出版了14种,在文论界很有影响。
《文学概论》一书的提纲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分成了五部分,即“作品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与“发展论”。要知道,将作品的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的起点,这在当时不失为文学理论的一种新的构成。分工时最后剩下“发展论”,归我来写。 “发展论”部分不能不探讨文学本质问题,所以让我颇费思量。过去文学理论把文学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称认识论文学观,但是这种文学观后来被简单化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人对这种哲学认识论、反映论文学观进行了大力批判与否定,在外国的各种文学研究方法、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各种文学观念蜂拥而来。有意识形态本性论、结构主义文学观、解构主义文学观、文学符号论、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论、文学感情论、文学表现论、文学生产论、文学接受论、读者反映论、文学现象学、文学是人学、文学心学论、主体性文学论、文学象征论、文学数学化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文学观等等。上面这些有关文学观念的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随便选择或附和一个观点十分容易。但是通过反复比较,感到它们是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的,我还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观最能宏观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在这个结构里,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等有着共同性即意识形态性,也是正确的。问题是后来一些人在阐述文学时,把各种意识形态的共性当成文学的惟一本性,而忽略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的审美特性,或是把审美特性当作附属性的、第二性的东西,因此需要恢复、强调文学审美特性的研究。歌德说过:他在观察事物时,总会注意它们的发生学过程,从而对它们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中谈到,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都可以“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在《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中,我试图寻找文学起源、发展的原点,于是就探讨了原始思维、神话意识、审美意识的关系,将审美意识视为逻辑起点,在其长期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存感受与感悟,先在口头形式中获得表现,成为一种审美意识形式。其后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具有独特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使审美意识获得书写、物化的形式;特别在话语、文字的多种结构的样式中,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意的审美与社会价值、意义、功能的复式结构的基本特征。随着人类社会结构进化与演变,在不同形态的制度社会中,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也显示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特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提出,力图做到论从史出,找回其自身的历史感。审美反映则贯穿于审美意识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后来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观念在文论界流行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观念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左”的思潮的批判,前几年这样的批判更为猛烈。不过新世纪的批判都是在马克思没有直接说过或是间接说过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或是厌恶文学与意识形态有着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两种批判殊途同归。这类批判罔顾原典、历史与传统,不承认文学观念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很难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对话的。
文学创作日趋多样,文学理论将发展下去
丁国旗: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学习理论,也需要理论的时代。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引发了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重大变化,一时理论与批评都失去了重心,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或许此时更需要人文学者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与态度。您觉得一个人文学者在现实社会中应该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来为自己的人生和学术安身立命?
钱中文: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追求物质、金钱成为社会理想,贬抑人文理性,失去信仰与诚信,引发了极为深刻的文化、精神危机。而人文理性在社会物化中经历着普遍的危机,使人类生存的底线屡遭破坏,一些哲学思潮推波助澜。有的人一听解构就惊惶异常,其实思想需要不断推进,新的思想需要不断建立,这个社会才有生气与活力。一些文学舆论,在反对伪崇高与满纸谎言的时候,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贬抑人文精神。文学艺术的感性,也变成了性感的流行与泛滥。面对这样的社会处境,我以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不能随波逐流,而应有一个建设性的立足点——反思人文、艺术创造的立足点,因此我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的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新的相互关系并实现它们;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即提倡一种可以去蔽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新的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并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几个方面,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在几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不断重复、反复出现的现象,而且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基本方面也是如此。新理性精神意在探讨人的生存与文化艺术意义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在物的挤压中,在反文化、反艺术的氛围中重建文化艺术的价值与精神,寻找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以我为主导、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兼容并包、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此说拓展了我自己的文学理论的思维空间,试图加强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的特性,也是我试图使文学理论介入当下社会生活的一个想法。有了这种立足点,我在人生与学术中确乎感到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处。
丁国旗: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引发的理论的困境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措手不及,那么,新世纪以后,理论的危机与反思却已指向了理论自身。记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希利斯·米勒一篇关于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是否还会继续存在的文章,借助新的电信时代的特点,他提出了“文学终结”的思想。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则在《理论之后》(2003)一书的开篇认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这实际也就是在宣布“理论的终结”,如果我们可以随性地将这两种“终结”嫁接在一起,似乎便可以直观地得出“文学理论的终结”问题。其实从后现代思潮兴起以来,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价值的被颠覆、中心的被消解,一切的一切都被裁入到平面化之中,理论的终结与消亡似乎真的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您怎么看?
钱中文:这些问题十分现实,也很尖锐。先说一下我对《理论之后》的理解。我以为伊格尔顿所说的理论,是针对上世纪20世纪80年代前欧美兴起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理论”而说的。文化理论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在喜好花样不断翻新的西方文化界已难以为继,于是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的种种主义已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阅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肉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们在图书馆里扎成一堆,勤奋地研究着像吸血鬼迷信、挖眼睛、电子人、淫秽电影这样耸人听闻的题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理论的终结”,而这种文化理论终结之后怎么办?所以叫做“理论之后”。虽然在西方,文化理论把文学理论也包括了进去,但实际上,在研究与课堂中却往往脱离开文学,而大谈泛文化现象,诸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些现象。上世纪末,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的始作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文化批评研究把文学理论架空了,把从文学讲授、研究中所应获得的精神、价值掏空了,于是他提出仍应回到文本,回到细读,当然这是一种新的回归。这样说来,我以为文化理论或批评在改变自己的形式之后还会存在下去,发展下去,而文学理论将会吸收文化批评中的合理成分而丰富自己,随着回归而改弦更张,因此不会发生“文学理论的终结”。
更重要的是,人的审美意识将会进一步发展,文学创作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而文学发展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20世纪初,一些自然科学家看到物质微观化了,以为物质消灭了。其实由于科学的发现,物质仅仅改变了其存在的形式,文学也是如此。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主要指的是,一些人把看到的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当作是文学自身的终结或死亡了。但是审美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是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人需要通过话语、文字的诗意结构,进行审美的创造、审美的欣赏、审美的阅读、审美的接受,同时从中反观自身,观照自己的精神,并提升它。我们还可以说,优秀的伟大的文学创作,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它维系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与更新。因此,纸质印刷的文学作品未来会缩小市场,但通过高技术的多样载体而出现的文学会照样存在与发展。
文学理论同样也会发展下去。其实,不少大作家也写思想精深的理论文章,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雨果、司汤达、席勒、鲁迅。伟大作家的理论著作都是每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没有这种财富,人们在精神上将会变得十分贫困与粗俗。此外,有些作家还有应对教学需要而写文学理论著作的,也别具一格,如老舍、郁达夫的文学概论等。理论与创作并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作家的思想理论高度,可以使其切入具有巨大震撼力的人的生存处境,助其达到创作的新水平。
泛文化研究难以解决
文学理论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丁国旗:今天,在信息化、全球化、消费符号化的社会背景下,文艺理论的处境的确举步维艰,它的不断扩容、越界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它发展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看到它正在被自身所消解。
钱中文:我对当今文学理论举步维艰的处境,深有同感,但我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其实,一般文学理论大体可包括马列文论、基础理论、古代文论、外国文论、比较文论等,现在又大大拓宽了范围:比如生态文学理论、网络文学文论、视觉文学理论,等等。
现在常常谈到文学理论的危机,理论死了,或是将陷入凋零与绝境,我以为这多半是指文学基础理论而说的,其他理论部门,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态势似乎比较缓和一些,因为相对来讲,它们都有研究的基本对象。文学基础理论问题多多:一,在当今文学形态发生大变化的时期,比如一般的文学创作变得形式多样,海量的作品价值不高,思想并不丰满,不易筛选。同时,网络文学、视觉文学的大力发展、生态文论的大力呼唤,作品数量的激增非过去所能想象。纸质刊物不登,在网络上自有一席之地,想象之奇特,思想之自由,形式之多样,真是前所未有,据说也有佳作,但还是凤毛麟角。总的说来审美趣味变得粗俗、廉价,人们更难以深入、确切地把握它们,理解它们的问题所在。因此文学批评滞后,而文学理论就更是如此,显得无能为力,严重地跟不上文学创作的实践。二,文学理论中的反本质主义问题。文化批评传入我国之后,这一思潮到新世纪更为活跃,它的反独断论,去中心化,很有影响,鼓舞了很多人。但是中国学者接过来后,他们自己的独断性、盲目性也很明显,如把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现象本质的研究,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批判,一时“反本质主义”呼声大作。对于本质主义要做具体分析,事物现象的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是有联系而又不同的两码事。事物现象的本质研究,在于弄清楚这一现象的性质、揭示现象后面隐蔽着的东西,以及它的真实形态与功能,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前景,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等。研究事物本质,是人的高级认识能力的表现,有何主义之有?“本质主义”则是我预设的都是对的,是一种自我定义为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是一种抱残守缺、不思进步的僵化思想,因此,怎么可以把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等量齐观呢?说实在的,很多事物本质的东西,我们不是研究的太多,而是难以研究,于是就拿文学理论来说事了!既然文学研究可以去探讨象征与修辞现象,多种体裁与形式现象,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共性特征,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探讨文学自身的本质特征呢?你说本质特征说不清楚,那么其他诸如象征、修辞、形式、体裁、流派、思潮都已一劳永逸地说清楚了吗?你不愿意研究文学本质,难道别人也不能研究吗?况且文学现象的本质研究,十分艰难,形成一个观念极为不易,很可能要凝聚研究者一生的心血才能做到,而且也不可能是终极真理,事物的真理性只能被不断地接近与认识。其实,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提供知识,也应该提供思想。当然,连思想也已市场化的今天,对于一些人来说,思想不思想也是无所谓的了。
丁国旗:现在很多学者都在撰文谈文学理论的文化转向,您是怎么看文艺理论界的文化研究热这一现象的?
钱中文:随着反本质主义的传播,事物的不确定性、平面化思潮大为流行。文化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被奉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规则。可是反本质主义的创新原则,使事物失去了质的规定性。文学是什么,它的边界在哪里,使得一些人模糊起来,于是掺和着不少外国人的观点,大声宣布今天的文学还未有定论,不少生活现象还未装入进去。这样,一时要以文化批评代替文学理论的呼声大为高涨。这种紧跟外国“诸子百家”的理论,使得文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探讨,一时处于变幻不定的状态,而日益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碎片与拼贴。针对当今的文化现象,可以开设讲座,但它们不是文学理论课程所要扩大的内容,如果把这些现象的讲解当作文学理论来讲,文学理论本身就真给掏空了,它原有的那些价值,都被转换了,被诸如时装设计、时尚打扮、服装展览、香车美女所替代了。现在一些朋友出版了好几种有关审美文化的著作,写得很有分量,也有前卫性,我很欣赏。设置审美文化的课程,倒正是适应了文学课程扩容、补充的需求。
一些学者认为,既然文学本质观念永远也说不清楚,那就应该放弃这类研究,进行看得见、摸得到的文学现象研究即可,于是特别在一些文学研究的杂志中,一些浅表性的实证主义式的研究得到了过分的重视。也有学者认为,现在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认为老师的责任不在于给学生以观念、定义,只需传授各种知识、任其发展即可。但是对于知识不予系统的梳理与综合,不予概括与定性,那么它们可能只是一些毫无联系的散乱现象,一堆知识的拼贴,而使知识失去应有的深度。由于文学中的泛文化研究的转向,放弃了理论的定性与归纳,甚至连文学本身也早被碎片化、拼贴化了。例如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一部1000多页的《新美国文学史》,其别开生面之处,就是这部文学史把小说家、诗人与拳击比赛、电影、私刑、控制论、里根、奥巴马等社会文化现象、政治人物和歌手,都当作文学史的写作对象,这种写法可能有着他们的理由(见《文艺报》)。这种现象目前在我国虽然还未出现,但说不定哪天我们也会看到这类著作的。
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在于回应时代的问题
丁国旗:我也觉得,文学理论应立足于文学,向外看一看,扩大一下眼界,并没有问题,但必须要守住自己的根,否则就会迷失自我。那么,您认为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我们该从何处给它找到合适的定位?这个定位又会是什么?
钱中文: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盛行之中,上述现象流行于中国文化、文学理论中,也有它的合理成分,它毕竟扩大了我们的知识,使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某种解放,这是最重要的方面。同时也有避免它的极端性而表现出当代建构性的一面,比如近期出版的几种文学概论一类的著作就是。这些著作普遍地就文学现象论述文学现象,建构各种关系,改变了原有文学理论的面貌,各有特色,力图有所出新,显示了文学理论的多样化与进步性。但这些著作也显出了平面化的特点,大叙事化倒是去掉了,而小叙事的出彩地方也不多,难以达到深思熟虑的哲理化高度。当然还有一些原有的《文学理论》修订本的出版,还有马工程教材中的《文学理论》的出版,有的长期打磨过的著作并不失其权威性。此外审美文化研究、网络文化理论研究、生态文学理论研究以及不少文学理论的专题性研究,都是很有成绩的,它们都要借助于文学基础理论而获得丰富。基础理论在艰难中行进,也显示了它的存在及其价值。
近几年来,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7大卷“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就是实绩之一。这套丛书,应该说是对20世纪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就、问题的一个总体性的详尽描述,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总结,一部20世纪全景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这样全面性的介绍、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创。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各个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命题,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多样性、当代性与开放性等特征。
改革开放之后,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被介绍到中国,在惟我独马的思想阴影下,那时是“西马非马”。现在看来,这是我们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一个整体去了解的缘故。一百多年来,我们看到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它们因国别、地域与文化传统而各自不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同于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德国的又迥异于美国的,什么缘故?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要与该国的文化实际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需要回答时代的问题;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不能使自己成为本土化的研究与本土化的理论,那它本身哪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哪会有什么生命力呢?现在对外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刚刚开始,就有人在放风,已经出现“新马化”倾向了,天要坍下来了!这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
除7卷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外,国内还有多卷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体论形态”等专题性研究丛书。这几套丛书很有新锐精神,一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死气沉沉的注释派和唯我独马派的文风,它们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思路,从而也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独创性、中国气派和强大的生命力。
文学理论中的消解现象是存在的,但只是某些人自身的消解。我以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上述成绩,就是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理由,以及我们在文学理论中的定位,因时间所限,不好展开了。
理论研究需要真诚与诚信
丁国旗:您的文学理论研究前后跨越了50多年,一定会有许多个人的体验与感悟,你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有些什么建议?您觉得文学理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您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钱中文:我认为,面对新的世纪,既要有对当下文学理论处境的焦虑与不安,也有期待与展望,我们理论界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
文学理论需要加强它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当今我们已处于网络文化之中,面对今天这样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文学基础理论确实身处窘境。如果我们肯定自己要在这块园地工作下去,那就需要有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去理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转型。文学理论需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需要多向文学批评家请教,实事求是地去阐明文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形式、新倾向,并在理论上给予恰当的概括。理论具有预言的功能,但它的常态则是去阐明已经发生的现象,确立相对稳定的规则。这需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去了解中外文学及理论的历史与现状,培养那种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当然,面对当今琳琅满目的文学现象,也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梳理、消化与积淀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研究者需要心向实际,同时又要避免当今相当流行的急功近利的学风。
在外国文论的吸收中,需要反省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本土意识与国际视域的关系。当今,外国文论的介绍十分普遍,有些国别文论、文论家的个案研究很有特色,相当深入。但是也要防止那种在介绍外国文论时,介绍者被外国文论所介绍的现象,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文学理论看成是外国文论的各种拼贴,任由感觉无选择的泛滥,跟在外国学者之后,拿他们的观点去引领我国文学理论的潮流,这极有可能成为各种无选择的理论的狂欢。我们每每阅读外国文学理论著作时总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本国的文学或是文化渊源相近的文学而展开的。最近出版的一套“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也是如此,都是与自身文论传统紧密相联的。因此我们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时,必须汇入世界的文明,吸收与融化外国文论的优点,在国际视域中进行。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建议。
在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中,也要检验我们的著述,是否具有历史感的品格,真诚与诚信的品格。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就会缺乏科学性与理论性,就会失去真诚与诚信,而难以取信于人。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历史感就是论从史出,论史并重,就是重视问题产生的现实性,它的历史文化语境、历史生成及其发展,它的历史传统。对于文学史来说,历史感就是尽可能地显示史实,揭示事实的真实面貌,它同样需要论从史出,使之史论相映。历史感要求作者的真诚,在实事求是的理论展开中,使其成果获得科学性,进而获得诚信。真诚是学者的一种主观品格,缺乏真诚,就有可能遮蔽历史真相,就有可能利用外力与话语权,歪曲历史,另有所图。这种恶劣作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生活风习,所以导致社会诚信丧尽,失却了凝聚力。当今某些新时期文艺学史著作,看似史作,实则缺乏历史感,让人感到历史似乎不是他们写的那个样子,因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都是在场的。这类文学理论史作,便只能是利用了话语权的缺乏诚信之作。
丁国旗:“真诚与诚信”对于人文学研究来讲,的确十分重要。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实的?学术研究如何才能获得良性的发展?
钱中文:学术的良性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多拿课题费当然很好,但很可能使学术变为依附。学术需要说出真话,使真诚融入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之中,那样才会产生具有独创精神的、原创性的、有价值的文化产品。有的人把重复、宣传当作学术,这使学术研究极为难堪。不过我在这里也要重复一下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然要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是最终昭示于世人、传之久远的,则是其充溢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文化创造。生产这种精神财富,应该在文化、学术中,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做起,进行原创性的创造。要坚持自己的声音,坚持那种具有学理精神的原创性声音,因为学术认同的只是独创。学术回应时代,也坚持自身的需求:学理的深化、完善与丰富。但是这种回应,应是绝对的个性化的,而不是重复与雷同。
当今文学理论介入的领域实在太多,中心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国际视域”与“中国问题”。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国际视域、传统资源与中国问题的相互激荡中,会不断地出现动态的、多样的理论新形态,这是我所热切期望的。
相关阅读:
- ·诗意的裁判与文艺的价值——文艺理论家胡经之访谈 (2013-09-10)
- ·韩东:我从来不想神化日常或者尘世(2023-04-23)
- ·陈众议:文学理论到了该清理的时候(2012-04-28)
- ·打通批评、理论与学术间的壁障 ——关于当下文学评论的对话(2018-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