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探询人性的深度——与周新民对话

艾 伟
周新民:艾伟老师,您好!您的出生地江南,文化底蕴深厚,能谈谈您的家乡么?
艾 伟:我出生在浙江上虞的农村,属于绍兴地区。我家乡就在曹娥江边上,江面宽阔。我老家以北大约三公里处就是当年谢安隐居之所——东山,“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就来自于此。李白当年到过此地,留下不少诗篇,“谢公东山十三春,傲然携妓出风尘”之类。曹娥江的上游就是剡溪,也是一条有文化有历史的著名的河流,比如“雪夜访戴”什么的。
绍兴这个地方是非常奇特的,它既有江南阴柔的一面,又有非常阳刚的一面。绍兴诞生了两种戏剧:一种叫越剧,细腻委婉,仿若小桥流水;一种是绍剧,高亢刚烈,有着北方的雄风,仿似秦腔。就像周家出了鲁迅和周作人,一个刚烈一个阴柔。绍兴这一地诞生了很多在中国历史上有受难情结的英雄是不奇怪的,近代如徐锡麟,女侠秋瑾等。
周新民:江南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江南子民,我注意到您中学就读的学校是春晖中学,这也是一所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学校。
艾 伟:是春晖中学孕育了我的文学梦。我的文学启蒙非常晚,真正对文学感兴趣是在读春晖中学以后。那是上虞一所著名的中学,现代文学史上一批大师级人物如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等在这所学校教过书。这些到过春晖的人物虽然斯人已去,但他们仿佛依旧活着,活在校园里。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文章同在。这在价值观上影响了我的选择,认定文学是一桩美好的事业。
周新民:除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春晖中学一定还孕育了您的文学梦吧。
艾 伟:我上春晖中学的时候,刚好是八十年代中初期,中国诗歌正处在朦胧诗时期,我经常去由叶圣陶题写馆名的图书馆去看文学期刊,各种各样的文学期刊都有。现在中学的阅览室大约不会有这么多文学期刊了吧?
周新民:现在应试教育盛行,一般中学阅览室只有和考试升学相关的书刊。
艾 伟:当时诗歌非常活跃,各种实践,各种对这种实践的赞美和批判。我记得艾青曾在《文学报》上发长文批判过朦胧诗。当时读完后觉得观点虽不同意,但批得很有激情,很有文采,同一般的批判还不一样。当然,如今也只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了,艾青批了什么都忘光了。
在春晖中学,我读了第一本外国小说,《牛虻》。一本非常有戏剧性的小说,当时读的时候觉得小说呈现的世界太迷人了。那时候那种牛虻式的革命在我的心里还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动荡、地下工作、破坏和其中洋溢的爱情,这些元素在当年的我的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当时,我大概有了对自己未来的想像,觉得这辈子如果能成为一个作家是幸福的事。但不是很明确。

艾伟小说《南方》
周新民:出生于江南,就读于春晖中学,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也对您的成长也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吧。您有怎样的“文革”记忆?
艾 伟:我出生于一九六六年。我晓事是在七十年代。七十年代虽然已是“文革”的后期,但“文革”的种种现象比如游行、批斗、大字报等依旧是社会生活最为戏剧性的主题。我要说的是,当我回忆这段岁月时,我的头脑中出现的不是疯狂,而是安静的气息,阳光灿烂,我们沐浴在领袖的光辉中。确是这样,在我童年时,我觉得毛泽东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这是我童年的真实感受。我曾同一位我的父辈长者谈过此一感受,他非常愤怒地反驳我,“文革”怎么会安静呢?那会儿我们受了多少苦,多折腾啊。我理解他的感受,因为他是个“右派”,在那个时代备受歧视。但任何童年都是快乐的,自由的,野生的,即使是在战乱年代,即使是在纳粹的集中营,童年可能依旧有着欢乐的底色。
当年,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只高音喇叭,它会准时传来北京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获知毛泽东又在新一次的路线斗争中取胜……总之都是欢欣鼓舞的消息。这让我感觉到全世界唯有中国人民才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狂热的军事爱好者,尚武是孩子们最高的美学,我们都希望自己有一套军装,一顶军帽,在我们眼里那是最美的服装,也是最高的荣耀。那时候,我及我的伙伴谈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这样的狂念只不过是语言喂养的结果。现在我回想童年时光,即使这样的狂念里也隐藏着诗性的成份,当然那是革命意识形态美学造就的诗意,但那时真的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周新民:这种“文革”记忆,日后如何影响了您的创作?在哪些作品中得以呈现?
艾 伟: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在回忆里总是最为鲜活的一部分,并且这些回忆里面有着人类生活的原型性的元素。这些回忆在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时它是会生长的。我的《乡村电影》就是这种回忆的结果。乡村电影一般在晒谷场上播放。有电影的日子就是乡村的节日,至少是我们孩子们的节日。在电影播放前,一些四类分子会被指派,把晒谷场打扫得一干二净。这种劳动是义务的,实际上具有侮辱性质。《乡村电影》这篇小说就建立在这些记忆之上。
《乡村电影》其实是一部关于人的尊严的小说。这也是我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同时,在这部小说里,我怀着对人性的基本信任。这是我最早的小说,但这个基调像种子一样已经埋下,在《风和日丽》中发扬广大了。在《风和日丽》中,虽然主人公命运多舛,但我还是试图书写出人心善好的一面,写出苦难生活中的温暖时光。
周新民:记得您曾说过,您在“文革”期间阅读了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画册、《一只绣花鞋》,它们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艾 伟:有一段日子,我突然对父母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去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有一次,我从家里翻出几本书,那是关于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画册,在这些书中还有一本手抄本,是郭沫若写的。郭沫若通过汉墓中出土的一粒西瓜籽推演了一个关于女墓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一口气把这手抄本读完了。我感到时空倒转,空气也同往日不一样了。我像是进入了幽深的历史之中,特别是女墓主的爱情故事,被郭写得缠绵悱恻,把我看得柔肠寸断。那段日子,我感到我的胸腔中似乎晃荡着一些温暖的水。
这故事把单调的日子填满了,好像这天地之间因为有了这些故事而变得温暖。那个手抄本开始在同学之间流传。那些日子,我们的眼睛发亮,觉得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向我们打开了。
一本手抄本出现,另一些手抄本跟着出现了。这世界就是这样,只要某一扇门打开,就会向你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幽深世界。不久我们搞到了第二本手抄本《一双绣花鞋》,这本集侦探、爱情、革命、凶杀于一炉的手抄本,一样让我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
现在回忆起来,我虽然在乡村生活,但一直在努力关注及想像外部的世界。当年,我们村庄还没通公路,公路在曹娥江的对面。我们坐在高大的堤坝上,看对面公路上的汽车。公路上的汽车一直在变化。早几年前,公路上出现的是笨重的苏式卡车。后来,国产的“东风”卡车多了起来。中日建交后,公路上会突然出现一辆漂亮的日本车。真的很漂亮,小巧,光滑,在阳光下一闪而过,就像昙花一现。虽然这种车非常夺人耳目,但我们还是给它起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叫“日本矮子车”。现在想起来,公路其实是一个象征,它一头连着遥远的地方,一头连着我们村庄。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遥远起来。

艾伟画作《一把手枪》
周新民:您是八十年代初期上大学的吧,那是一个文学信徒的理想时代。您能谈谈您大学期间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活动情况么?
艾 伟:我大学期间不太合群,现在也依旧如此,呵。我是在重庆读的大学,学的是工科。当时是八十年代,文学理所当然是校园中最热闹最醒目的内容之一。当年诗歌在重庆是非常热闹的,各大学之间流传自印的诗报,我在诗报上读到很多口语诗歌,很实践性很观念的那种。我虽然不写诗,这辈子也就借小说人物写过几首,但见证这些活动无论如何对我立志于写作有促进作用。在大学期间,我极不喜欢我的专业,基本上不太上课,每天睡懒觉,为了应付考试,都是在每学期最后一个月才开始打开课本,那时候课本还是全新的。我因此对考试这件事有莫名的恐惧。我毕业后大约有十多年,一直有一个噩梦跟着我,就是又进入考场,总是梦见自己什么也答不出来,然后在一身冷汗中惊醒。最近几年不再做此类噩梦了。八十年代无论如何是有光芒的年代,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新鲜事物,心灵完全呈开放状态,不拒绝任何东西,也不讲功利,也只有在那种气氛下,才会去读一些“无用”之书。在大学二年级,有一本书令我无比震憾,它就是《百年孤独》,这本书颠覆了我既有的文学框框。后来我读期刊时发现这本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如此大,好多中国作家堪称其代表作的作品都是《百年孤独》催生的结果。
周新民:您大学期间学的是工科,工科背景对您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哪些“便利”。
艾 伟:我学工科不是因为我喜欢,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文科,但我们当年有一个观念,认为只有笨孩子才学文科。在文理科分班时,班主任让我选择文科,但我坚决选择了理科。我自认为数理化也不错。当时是很骄傲的一种心态下的选择。另外,文科要背的东西太多,觉得头痛。
我想说的是,我其实只不过是选择了一门错误的专业。当年在学那专业时,我脑子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戴着工程帽在施工现场做一名工程师。相反,满脑子是关于做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自我想象。不过,毕业后几年,我确实做过一段日子的工程师,那也是我感到最痛苦的一段日子。我在内心深处厌烦那种琐碎的日常事务。
如果一定要认为工科背景对我写作带来“便利”,那可能在小说的结构上我会想得更清楚一点,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像造一座房子,我会找一些足以让房子立起来的柱子,然后再考虑细部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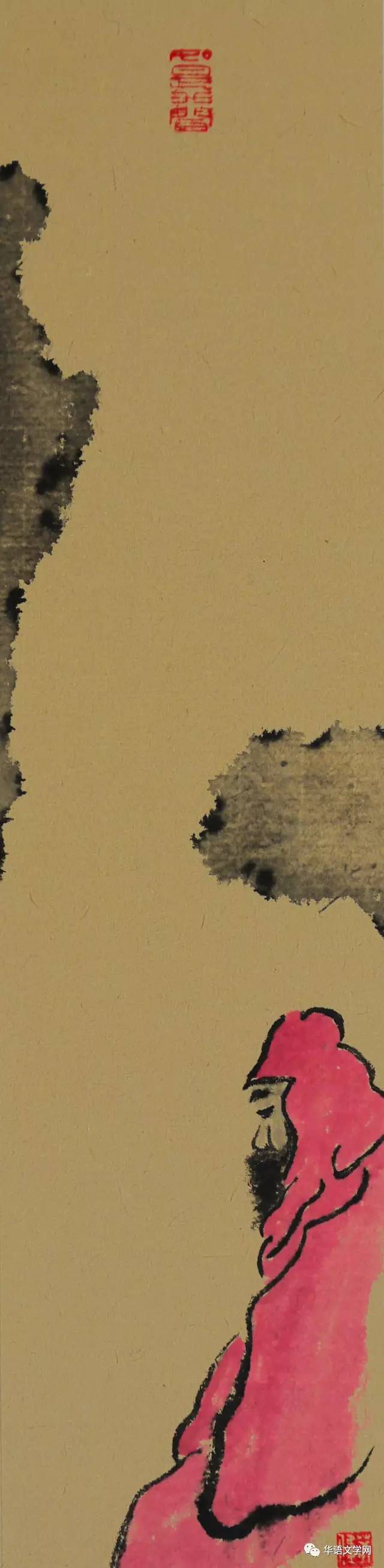
艾伟画作《达摩》
周新民:你们这代作家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您认为大学教育对一个作家的成长重要么?为什么?
艾 伟:我想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读大学,我应该还在乡村,在乡村那样的闭塞环境下大约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另外,大学的课堂上虽然没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你会从朋友、同学身上看到听到学到很多东西,有时候可能是一句话,会打开一个你从未关注过的世界。当年,学校里有很多关于新思想的讲座,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至少八十年代的大学经历是有意义的,回忆起来也是充满了激情和创造。现在大学教育怎么样,我不知道。
周新民:现在的大学生被各种考试所折磨,创造性和激情被催毁殆尽。回想下,您觉得哪些中外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较深的影响?请具体谈谈。
艾 伟:我在写作之前读得书也不算太多。倒是看了很多电影。那时候重庆沙平坝有一个小影院,每天下午都放小众电影或经典老片。有很多文学名著改编的老电影。有些我读过,有些是先看了电影后再读。
大学期间也有一些写作上的训练,但当时的感觉是自己很难完成一部作品。我真正写作是工作以后,刚好有段日子没任何事干,就开始写作。一九九六年才在《花城》发表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我在我们这一代出道比较晚,甚至没赶上新生代当红时期。我生活在宁波,同文学界没任何联系,完全属于自由投稿。感谢当年《花城》编辑林宋瑜编发了《少年杨淇佩着刀》。这之后,我开始在《收获》和《人民文学》发表作品。
大约在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好满一百年,几个朋友说做一本百年获奖作家作品阅读的书。那段日子,我集中阅读了一批作家的作品,并写了一组阅读笔记。后来这本书起名为《孤独的慰藉》出版了。
说到作家的影响,在我的具体的作品中还真是很难找到,有时候,我喜欢的作家的风格也不一定投射到我的作品中。所以说,我只能说我喜欢的作家。这些作家我想大家都喜欢,属于举世公认的吧,古典的有托尔斯泰、简·奥斯汀、哈代、萨克雷、司汤达。二十世纪的当然读得更多些,那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精神资源,有福克纳、马尔克斯、加缪、卡夫卡等一长串。如果要在这些作家中选择二位,我会选择托尔斯泰和福克纳。另外,我喜欢很多作家不喜欢的米兰·昆德拉,我喜欢他处理社会主义经验的方式,我认为至今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写作还没有超过他。
周新民:《越野赛跑》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您在开始写长篇小说时,碰到最大的困难时什么?
艾 伟:这是我第一部长篇,一定是野心之作。我当时觉得自己的文学训练差不多了,跃跃欲试,想写一部能全面实现我当时文学理想的作品。那个年代文学还是具备先锋精神的,对文本的创新还有热情。当然《越野赛跑》不是真正意义的实践文本,它的根本目的还是试图处理我们“文革”以来的经验,只是用一种写实和超现实结合的方式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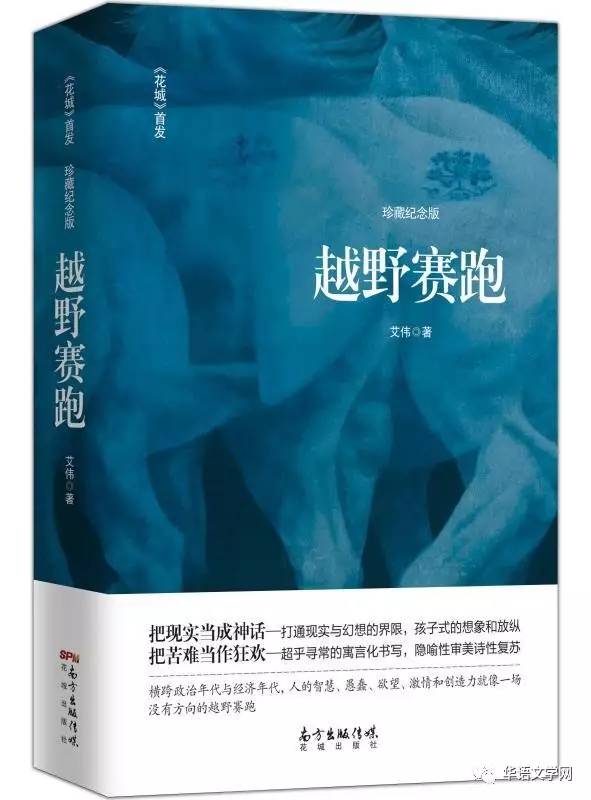
这部小说写作时多次出现过困难。写步年和小荷花发配到天柱时,我一时难以书写。这时,我发现了灵魂,那些在现在世界中正在被批斗被折磨的四类分子,他们的灵魂寄居在天柱。这样,天柱的象征性迅速得以拓展。另外一个困难是改革开放阶段。因为时间就近,这一阶段的书写要具备神话特征还是具有难度的。但后来“天柱”还是帮了我的大忙。“四人帮”粉碎,马发情了。这当然是我早已想好的一个隐喻。“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步年就带着马去交配,在天柱,他看到一个“未来世界”。那儿高楼林立,欲望无边,太阳从西边出,水从低向高处流。它映照出了即将来的一个经济年代。后来,“文革”时失踪的老金法以灵魂的方式回来了,但他已是一个欲望的灵魂。
无论是“文革”年代还是开放年代,我的看法是它们其实互为倒影的一种关系,表面上看,一切都是反向的,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完全一致。
周新民:理解精辟,所谓没有“文革”,何来新时期?《越野赛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小白马”和“天柱”。您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什么?
艾 伟:我的小说往往起源于记忆中的某个场景。这些场景背后的现实逻辑也许早已淡忘,但场景本身总是被我莫名其妙地反复记起。我把这些场景当作我生命的某个密码。我相信其中一定蕴藏着这个世界的秘密。我还相信,这些场景还有其生长能力,它最终会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叙事世界。
《越野赛跑》同样来自这样的一个场景:我童年时,有一天,一支军队突然开进了村庄,然后,我看见路上出现了奔跑的马,骑在马背上的是身穿绿色军装的解放军,他腰间佩着的手枪系着一条红色的丝带。1999年,这个场景在不断地膨胀、变幻,就好像一粒种子落入热带,迅速繁殖,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在这种时候,你是无法阻挡建立一个虚构世界的诱惑的。
“天柱”这个意像受《红梦楼》太虚幻景的启发。但它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在村庄边上,一个到处都是昆虫的地方。我把“天柱”当成是灵魂的栖息地,灵魂自由出没之所。人的肉体在人间受难,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尊严可以留在“天柱”。
关于这匹白马,我当时希望用这匹不停奔跑着的马去隐喻人类生活的某种境况。在技术上,他联结着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
周新民:《越野赛跑》的叙述独具匠心,我看到了您在保持先锋小说的探索精神的同时,已经开始融汇先锋小说和传统写作的综合优势。《越野赛跑》,一方面注重象征艺术的运用,另一方面在叙述上却采用按时间顺序来结构作品,话语方式也不刻意追求创新。您为何有这样的艺术安排呢?
艾 伟:这里面其实有对自己的挑战。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它其实是抽像了现实历史的,它不具体落实在现实历史事件上。这样的书写会更自由一些。我当时却要求自己,必须和我们的历史扣在一起,要求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准确,是可以查考的,在此基础上,再飞翔起来,夸张变形。所以,这个作品其实是写实和变形结合的作品。作品中运用了完全写实的白描等手法,把神话和事实放在一起,同等看待。这其实是一种类似童话的写作方式,用孩子式的口吻讲述,放纵想象,道听途说。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转述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读者非常容易相信转述。我还由此想,在人类原初,那些神话其实都是一次次转述的产物。事件和人物在转述时,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周新民:《越野赛跑》虽是您长篇小说创作的起步,但是起点很高。《爱人同志》则把探索的笔触伸向人性的深处,《爱人同志》构筑了社会伦理与人性之间冲突,在冲突中彰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在我看来,《越野赛跑》和《爱人同志》之间的跨度很大。从《越野赛跑》到《爱人同志》的探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艾 伟:《越野赛跑》是一则寓言。但我发现寓言写作是有其局限性的。你很难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人的复杂性。就像《阿Q正传》这样的经典作品,其实阿Q展示的人性也是非常简单的,简单到阿Q只是一个符号。这是我在写作《越野赛跑》不满足的地方。我也试图把冯步年、冯步青写得更复杂些,但在那样一种叙述和格局中,我还是很难往人性深处走。
我于是决定换一种写法,通过对人性深处的勘探,把时代的印记内在化,时代的阵痛完全落实到个人的楚痛中来。于是有了《爱人同志》这部小说的写作。
八十年代初,“自卫反击战”后,当年有很多女学生爱上残疾英雄的故事。报纸广播和电视连篇累牍地渲染这样的故事,当然在主流媒体上这些故事成了王子和公主终成眷属的童话。我在2000年想起了这段往事,我当然绝不会写一个童话故事,我的故事是从这个童话结束的地方开始。我要探讨的是,这对夫妻婚后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度过及适应这十多年来中国的迅捷变化?这十多年,中国开始走上市场经济,原有的道德理想主义慢慢破产,旧有的英雄人物迅速地被新的市场英雄所取代。我感到这个事件和当事人身上隐含着的太多人性漩涡和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
另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无论从内心到身体都经历了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记录这个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痛史。由此我发现通过人性内部的探索和处理,依旧可以成为一个寓言,这个寓言可能更有深度。
周新民:您这样一解读《爱人同志》,就把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高度概括化了。在我看来,一部《爱人同志》其实也是一部近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史。在这历史的变迁中,您把人性的深度揭示出来了,触摸到了人性中许多微妙、复杂的东西。《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即是这样的作品。《爱人同志》的中刘亚军是施暴(性暴力)的一方,而张小影则是默默地承受暴力的一方。《爱人有罪》似乎延续了这个叙述结构。《爱人有罪》也构筑了一对施暴与受暴的双双。鲁建是施暴的一方,而俞智丽则是受暴的一方。奇怪的是,《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中的受暴一方,都选择了承受,并享受了受暴的快感。这就是“虐恋”。据西方文化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虐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您怎样理解虐恋的?您为什么要再三书写“虐恋”?

艾 伟:张小影和俞智丽还是有差异的。俞智丽是完全的承受,鲁建则对俞智丽是爱恨交加,他在社会上所受到的冤屈投射到了两人的性关系上。刘亚军和张小影不是,张小影自己也是对刘亚军大打出手的,刘亚军和张小影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普通人家的夫妻关系,当生活日复一日地暗淡下去时,他们通过暴力的方式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和不甘。暴力会暂时平复这种伤痛,让他们进入美妙的性爱。这是他们相濡以沫的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张小影的忍让确实多一些。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我觉得“暴力”确是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之一。这涉及的中国人的幸福观。幸福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精神结构,在西方,那个顶尖坐着一位神,但在中国完全是世俗的,顶尖坐着的是人——过去是皇帝,现在是权力。所以,中国人的精神结构本质上构成一个父子关系。平和的父子关系激发不了强烈的情感,只有在冲突中,父亲对儿子施暴后,父亲再摸儿子的头,儿子才会涌出强烈的幸福感。当然这种结构在基督教里也同样存在,面对神,只有让自己受苦、受难,灵魂才会有感动。所不同的是,西方精神上的父亲只有神,而中国人精神上的父亲是人,并且是无数握有权力的人,中国人精神结构中的这种父子关系使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超乎寻常的艰难,因为这样的父子关系难以产生平等的观念。
说到“虐恋”,虽然我写作时并无此意,如果一定要进行解读,你可以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这种文化本身就是既暴虐,却又是人人依赖和爱恋的。
周新民:“爱人三部曲”第三部“爱人再见”写作进展如何?它要探讨的主题是什么?
艾 伟:这三部曲大致有个类似的主题,就是探讨两性之间的阴影。当然这阴影和时代有密切的关系。第三部故事发生时间更早些,四九年前后,也是围绕着男女关系展开吧,大致想探寻一九四九年革命意识形态开始对人心进行管理时的人的状况。这是我早年的构想,但目前还没写出来。我希望最终能写出它,完成三部曲的愿望。
周新民:我觉得您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心理活动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和表现,您能谈谈哪些心理学家对您产生过影响?
艾 伟:我还真是没好好学过什么心理学。大学时期读弗洛伊德和普通的心理学也不一样。作家某种程度上靠直觉。靠以己度人。靠对人的可能性的想象。对人的细微处的准确把握其实是写作的时候产生的,是即性的产物,也可称之为灵感。写作的时候,我的体会时,我比平时要警觉得多,我在那个虚构世界里看到的听到的也比现实世界要多。我写作时经常想像自己“要像狼一样警觉”。在各种可能的关系中挖掘更丰富的东西,或在不可能中展开可能性。
周新民:“要像狼一样警觉”的写作状态非常贴近您作品呈现出来的感觉。《风和日丽》一改《爱人同志》和《爱人有罪》的窥探伦理与人性的叙述模式,转而从社会历史角度来思考人性问题。您为什么变换了考察人性的角度?
艾 伟:我自己觉得我的思考方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实《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这样的作品,社会历史一直存在。我相信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他要把他所处的时代写出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所谓的“纯文学”。《风和日丽》只是在时间上跨度更长一些,五十年,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叙写了很多历史。其实在这个作品中关于历史的描写非常少。
《风和日丽》是我最近的作品,一定代表着我最新的对长篇小说的思考。我认为长篇小说有最基本的价值元素,这些元素是:复杂的人物、丰富的情感和令人喟叹的命运感。
“先锋”以来,深度模式一直控制着中国作家,这种对所谓深刻的追求导致在小说里只有冰冷的理性。小说不是写诗,不是靠几个意象就可以完成。深度也不是靠结构、靠语言即可以抵达。小说必须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欢欣和血泪,写出命运的吊诡,写出众多力量作用在人性中的波澜。小说里有作家的思想背景,但决不是思想,小说不是去说明什么伟大的发现或对历史重新书写,小说永远关注人在时代意志下的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和处境。小说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分析的。我对好小说的评判标准是:阅读完一部小说,像是重新活了一次,会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会拉远,对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改变。即使只是一刹那的改变,也够了,因为这个坚硬的纹丝不动的世界终于有了温暖的柔软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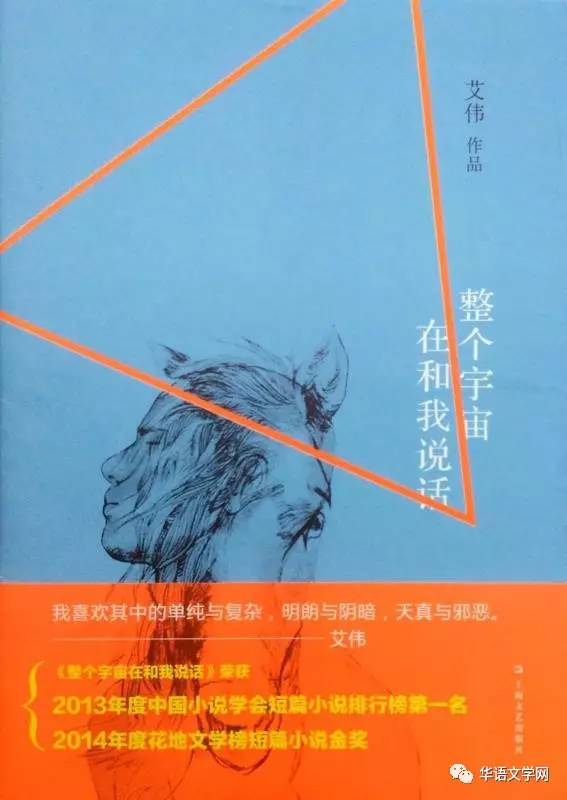
艾伟作品《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
周新民: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风和日丽》的双线合一的结构模式:“寻父”——“认父”——“审父”——“弑父”——“认父”和革命的“认同“——”“审视”——“再认同”两重结构相耦合。这体现了您对中国革命史的个人思考。1990年代盛行解构中国革命小说叙述潮流,《风和日丽》则是对中国革命史的再叙述。您是怎样理解中国革命史的?
艾 伟:我倒是在理论上去谈革命也没多大兴趣。我的出发点只不过是想考察革命对个人生命及人性的影响。这影响至今深远。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孩子,革命的那套思维方式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具体到当今知识界,无论左右,他们的思维方式大致差不多,都难免受到革命及其逻辑的影响。即使他在言辞上非常普世价值,但当你落实到那个具体的人时,往往令人失望。仿佛他的言说只是启蒙别人,他自己无需如此。
在《风和日丽》中有三代革命者,法国留学归来的开国将军伊泽桂,“文革”造反派伍思岷,以及伍思岷的儿子也是尹泽桂的外孙伍天安。他们是三位一体。伍天安死在逃亡之路上。革命自己处决了自己的儿女。这就是我对革命的看法。革命已破产了。因此,我觉得我在思想上根本没“认同”一说。但我说过,作家的立场不是政治正确,也不是历史正确,他的立场只是人的立场。所以在对将军的处理上,作为一个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我确实对将军有“同情之理解”,我认为他可能是历史意志的创造者,但他同样也是历史洪流中的牺牲者。个人怎么能敌得过历史?
周新民:作家处理历史的方式和学者是有差异的。您的对革命的一些认识很有见地。解构中国革命史,其实是对中国革命史的消费行为,值得警惕。《风和日丽》其实也体现了对消费革命史的担心。您是怎么来看待当下消费革命史的现象的。
艾 伟:最后将军住过的地方成为红色旅游点,在我看来是一个“反讽”。关于革命意识形态,我已有长文反思,我这里简述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认为革命曾经是我们的一尊神,但如今这尊神已倒下,革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语汇,也随着意识形态的破产而破产。现在的问题是,曾不见容于革命意识形态的“私”已完全合法化,但国家却仍沿用已失效的不被中国人认同了的意识形态管理人心,人心的管理系统无效了。因为革命意识形态天然的排它性,国家暂时无法用别的人心管理系统如儒教、基督教、佛教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对人心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现阶段中国社会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像小悦悦事件、毒奶粉事件等,以后还会更严重。
周新民:与您的这种忧心相反,《风和日丽》呈现出分外分明温暖色调,就像风和日丽的阳光照进人心的一样。这和您前期的小说注重探讨人性的幽暗有所不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艾 伟:我认为一部好小说中,它的黑暗和光亮是需要有平衡的。比如《红与黑》,其主人公于连十分复杂,《红与黑》里的于连,是如此复杂,他在人类价值的两极,是一个矛盾的产物:他是如此自私又是如此慷慨,如此自卑又是如此骄傲,如此胆怯又是如此勇敢,如此理智又是如此疯狂,他是个既黑暗又光明的人物。但基本上于连在这部小说中更多的还是人类黑暗的部分。但另一个人物,雷纳尔夫人就不一样了,绝对是光明的,她是个善良的人,她对于连带着母性的无私的爱,她在小说里几乎没有缺点,是个女神。雷纳尔夫人的存在使这部小说的光亮与阴影得以平衡。如果没有这个夫人,这部小说的魅力是要大打折扣的。她的魅力来自哪儿呢?其实来自于人类的正面价值。这很奇怪,当作家在小说当中对人类正面价值肯定的时候,对读者就有很强的感染力。
我已人到中年,对世界的看法会比以前更公允些,并且我认为一部小说要有多元的价值取向,既要对人类黑暗的层面进行探索,又要对人类光明的层面进行书写。我觉得这个平衡在中国当下文学当中可能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过多地关注那个黑暗层面。
相关阅读:
- ·没有精神深度的文学没有价值(2015-04-09)
- ·海飞:人性是小说与剧本共同的焦点(2012-08-20)
- ·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文学之光——作家迟子建访谈(2013-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