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能仅仅在语言中冒险"

Q1
伯竑桥:西渡老师您好!很荣幸对您做这样一个访谈。我想起苏格拉底《裴多》《会饮》等篇章中师生间的交谈与照亮。过去两年里,我陆续拜读了您从1990年代到近年的主要文章,深感老师的诗学观念之独树一帜。让我格外认同的是,这种诗学观念不是从概念出发、依赖推理得出的,而是与您对既往人生和生命历程的体认密切相关。这次访谈我想从您的诗学观念和写作出发,并进一步讨论当下诗歌现场的一些问题。
您曾经提出,1980年代写作实绩最出色的几位诗人,大体上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主流”以外的诗人,譬如骆一禾、海子。当下汉语诗歌相对而言的“主流”是什么?在现在的语境下,批评家和诗人同行们,应该依靠什么去从喧嚣里辨认一位可能相当珍贵的当代诗人?
西 渡:1980乃至1990年代的诗歌都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以及与之相伴的口号、旗帜,而最近二十年的诗界几乎是静悄悄的,没有口号,没有旗帜,没有聚光灯,也没有舞台,到去年才有“未来诗学”引发的一阵喧嚷。我以为这种情况才是正常的。在新世纪以来的写作中,我只看到一个一个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我们现在回看1980年代,那些口号、旗帜连同它们一度占领的山头都消失了,留下来的是几个出色的诗人。而这几个诗人当时差不多都在中心和旋涡之外,他们在观念和写作上都和中心保持了距离。韩东算是中心中的人物吧,但韩东的写作并不遵循口号,包括他自己的口号,譬如“诗到语言为止”之类。他的写作要比这类口号更复杂、更丰富,也更微妙。而那些相信了他的口号的诗人,都“死”在他的口号之下了。诗根植于存在,根植于诗人独异的生命及其与世界的碰撞,按照流行的观念、按照别人据于自己的境遇提出的口号来规限自己的写作,不过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的新例。水是流动的,兔子是活的,难道属灵的诗还不如水和兔子好动吗?
我真的不清楚当下诗歌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应该向你请教,因为你离现场更近。我对当下诗坛的观感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安静。诗人们差不多各写各的。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比朦胧诗那一代、第三代诗人都安静。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关注少了,但也是年轻诗人的自我要求吧。吵吵嚷嚷的诗人不是没有,但翻腾不起什么水花,也得不到同龄人的认可。安静地写,安静地办刊物,安静地出诗集,是这代年轻人的特点。这种安静的品质给诗人按照自己的内在模样成长提供了时间和空间。1980年代的人们都急吼吼的,像是在赶一趟过时不候的火车。从那个年代来说,也有他们的道理。朦胧诗、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就是这样一些火车。赶上了,就扬名立万,赶不上,下一趟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朦胧诗时代,一两首诗就可以让诗人的声名传遍大江南北,第三代也还有这样的机会。1986年以后,这样的火车就停掉了。诗人们都在抱怨诗歌的边缘化,其实不过是停掉了这样的火车。连火车站都拆迁了。但停掉有停掉的好处。看看1980年代那些赶上了车的又怎么样呢?多数人还是掉下来了。少数还在车上的,是因为火车本来就是他们的。停掉以后,诗人的心态多少恢复了正常。该散的都散了,确实想赶路的,就自己走吧,或者回家造自己的车。这样,诗人的数量少了,留下来的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或者确实是“不去写就会死”的那些人,但诱惑也还是有的。
批评家的职责就是去发现这样的诗人,发现那些仍然无名而显示了潜力的诗人。当然,也不乏成熟的诗人仍然处于无名的状态,仍然是诗坛的陌生者。批评家、编辑都应该这样做:阅读年轻人、无名诗人的作品时多一点耐心。我在一些评奖活动中特别强调要向诗坛的陌生者开放,至少给予平等的机会,就是为此。除了责任,发现陌生者也是对批评家眼光和能力的考验。其实,好的批评家、好的编辑是愿意向陌生者开放的,但落在每个诗人身上的机会是不均等的。安静的诗人们也需要跨出一步,为了让你的诗被人见到。
Q2
伯竑桥:您数年来反复倡导一种“幸福诗学”的可能性,认为当代诗中过量的消极元素和疯狂形象在不断削弱诗人的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它们其实是种毒素,也对诗歌的天然面貌有遮蔽,那么根据这条线索,您会主张怎样去重新整理1980年代以降的当代诗歌遗产?
西 渡:2009年我写了一篇题为“幸福的诗学”的随笔,这可以说是我提倡“幸福诗学”的开始。到现在十五年了。它源于我对中国当代诗进程和开始于波德莱尔的现代诗进程的反思。爱伦·坡、波德莱尔以来,现代诗的主流就是一种否定精神。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其主流也是一种否定精神,与世界现代诗潮的流向是一致的。朦胧诗是从“我不相信”生发出来的。但北岛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也就是说,朦胧诗的否定其实包含了一个肯定的指向,但第三代诗人并没有继承这个肯定的指向,而选择性地放大了朦胧诗的否定意向,把否定视为诗的根本精神。这种否定既指向内容,也指向形式,所以在两方面,它都难以建立。到了1990年代,一些诗人意识到问题,试图在形式上有所建立,转向技术主义,而内容上更趋于空洞化,提前实践了一种AI式的写作,这就是八九十年代当代诗的主流。但在主流之外,其实存在一种取径完全不同的写作,最典型的就是骆一禾的诗观及其写作实践。骆一禾说诗歌乃是创世的“是”字,诗的创造和创世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对于骆一禾来说,诗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而生命乃是“博大生命”,是和人类、宇宙的大相通的。与骆一禾取向相近的是昌耀、海子、戈麦等诗人。海子同样是肯定生命的诗人,也是肯定幸福的诗人。臧棣曾撰文讨论海子诗歌中的幸福主题,有力地纠正了一个时期对海子的误读。戈麦表面上厌世、绝望,但这种厌世、绝望是基于对生命的更高期待,也是对生命价值的守护。诗是对生命的最高肯定,在戈麦那里,和在骆一禾那里,是完全一样的。是对生命的渴望和拥有,导致了戈麦对肉身的毁弃。也是臧棣,写过一首题为“戈麦”的诗。在这首诗中,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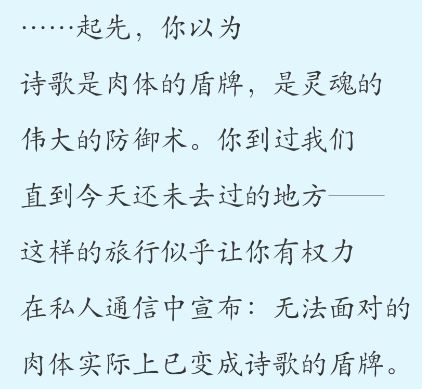
“肉身变成诗歌的盾牌”,戈麦实实在在地以肉体捍卫了诗歌,捍卫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但海子、戈麦相继自杀的事实也表明了肯定的、“是”的诗学在这个世界的孤立处境。
1990年代以后,这种否定诗学已面临巨大困境。非非、莽汉、撒娇、大学生诗派在1980年代就已经死了,也并未留下多少积极的诗歌遗产。“90年代诗歌”一度拥有的形式活力到1990年代末也成了强弩之末,难以为继。怎么克服当代诗歌的这个困境?我认为只有否定这种否定诗学,重新激活并提倡骆一禾、昌耀、海子、戈麦诗歌中闪耀着光芒的肯定精神,才是出路。当然,对这些诗人的诗歌遗产也需要以一种肯定的、创造的眼光重新衡量,以一种骆一禾所说的“辽阔胸怀”,以一种“幸福诗学”为目标,对其中极端的、绝望的、否定的因素进行清理,甚至也需要一场心灵和心智的革命。这是歌德对维特的革命,杜甫对李白的革命。我们知道,海子最心仪的诗人其实是歌德。那么,我们就需要对那些阻止海子成为歌德的因素进行反思和清理。当代诗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青春之歌”后,或许将迎来一个歌德时代。
当然,提倡一种肯定的写作并不是彻底抛弃当代诗歌的“否定”精神。在我看来,一种当代的肯定诗歌首先必须能够践行一种艰难的、持续的否定行动。因为当代生活本身是以否定为中心的,诗歌要走向肯定,必先对此否定。所以,骆一禾提出“必要之恶”“于罪恶我有健康的竞技”。阿尔托说,善是一种意志,是一种行为的结果,而恶是永恒存在的。所以,书写肯定的诗实际上是一种战斗。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卡夫卡列入否定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卡夫卡是一个真正为肯定而行动的人,他的全部否定都有肯定的指向。他说:“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卡夫卡说的不就是一种幸福诗学吗?但是不要忘记,幸福中也包括痛苦,正如我说的,肯定中已包含了否定。
Q3
伯竑桥:在《灵魂的未来》批评集里,您多次强调,诗人首先应该是常人、普通人、劳作者,诗人角色不意味着有更多特权,反而意味着有更多的责任。我深以为然。然而在现实层面,当下的汉语诗歌生态里,高声强调自己是诗人继而行事罔顾基本公序良俗的大有人在,诗歌界内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数见不鲜,这也加深了公众乃至文学界对诗人与诗歌的误解和敌意。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思考提出这样的呼吁呢?这种呼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能为更多写作者所接受,是否和前述“清理当代诗中的负面毒素”有关?
西 渡:这首先是一种自我认知吧。自己太普通了,太平常了,想要特殊化也特殊不起来。按照那种天才的说法,我怎么会是一个诗人呢?同时,我也认为作为天才被照顾、被“包养”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与我对平等、自由的看法完全相悖。被照顾,可能是你高看自己,让别人侍奉你,但也可以是别人看低你,要你侍奉别人。前者如一些仰赖异性照料的诗人,后者如历史上的宫廷诗人——这类诗人事实上到现在也没有绝迹。无论哪种情况,其中都不存在平等,也不存在自由。其次,也是对诗的一种认知。我想要一种普遍的诗。我认为它只能产生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每一种身份都会赋予一种特殊的视角,也就遮蔽了这视角之外的事物。只有普通人的视角遮蔽最少。因为普通,所以坦诚;因为普通,偏见最少;因为普通,抵达最远。诗人唯一与普通人有所区别的,大概就是他的感受更完整、更敏锐、更强烈、更开放。圣-琼·佩斯有一句话,经骆一禾的引用,在当代诗界变得很有名:“诗人就是那些不能还原为人的人。”我的意见相反,诗人首先要还原为人,从一个囿限于各种身份的人还原为一个普通人。我希望自己以无所依恃的“人”的身份与人相见,与世界相见,我的诗所表现的就是“人”在世界上的存在和遭遇。我相信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才是完整的,也才是最值得书写的。享受天才的生活固然让人羡慕,但也会错过很多普通人的乐趣,特别是普通人的忧愁、烦恼和痛苦。这种忧愁痛苦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谋生的艰辛。一个人不知道谋生的艰辛,就很难说拥有完整的人生。不要以为做普通人容易。人人各怀自己身份的偏见,成为普通人,就是要克服各种身份的偏见,成为“人”。这实际上是很高的要求。
我也希望我的诗可以通向更多的人。我不希望我的读者是特殊身份的人,希望他们消除各种身份偏见,以普通人的身份与诗相见。
我既然是一个普通人,也就并不指望我的意见会被人接受。我想,很多诗人需要在现实中碰上许多壁,才会接受诗人是普通人这个事实。如果这还不行,那也真是无可如何了。
Q4
伯竑桥:您曾在《历史意识与90年代诗歌写作》中写道,1940年代和1990年代有种对应关系,但实践者的历史和旁观者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不同在于,1940年代的穆旦是历史最一线的参与者。由此,作为诗人,也作为批评家,您怎么理解写作者和自己所处时代的关系?具体而言,如果大家参与时代现实的能力和意愿在减弱,那么当下的汉语诗人会不会正在逐渐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旁观者呢?
西 渡:中国诗人多是生活的旁观者。写田园诗的不下地,写边塞诗的不从军,写民间的在庙堂……这种情况到现代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抗战十几年,诗人、作家其实大都生活在安全的地方,像穆旦这样亲身经历战场的诗人是少数。诗人和时代的关系取决于身体,也取决于心灵。在这两方面,穆旦都是稀有的。所以,穆旦的诗一直无可替代。
对于真正的诗人,时代是一个内部的事件。好像人人都生活在时代中,但对于多数人,时代只是外部的事件,他对于这些事件有认知,有某种理智的认识,但并没有身体性的体验。他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时代,只要那些事件、变故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就一切如故。他也许把时代当作题材乃至主题,但他这么做纯粹出于理智原因。读这种诗人的诗,你只能感受到一种智力的活动,诗人的心并不在题材中,也不在主题中。这就是很多口口声声拥抱时代的诗人和时代的关系。而真正的诗人必以全部的身体和心灵参与时代,时代对于他是一个内部事件,发生在他的身体和心灵中。穆旦是这样的诗人,戈麦也是这样的诗人。戈麦的诗很少直接提及时代,几乎不以时代的重要事件作题材,但时代的不安、紧张、动荡,全在他的诗中。因为他和时代的关系是身体性的,他全部的情绪、感觉都是时代的。
有批评认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全面犬儒化了。我大致同意这一判断,但我并不认为知识分子自身应该为这一犬儒化负主要责任。我认为,对于诗的事业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诗人失去了感应现实的能力。一些诗人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代的痛苦,无数人的呻吟,他们根本听不到,更别说事物的痛苦了。史蒂文斯说,衡量诗人就是衡量他对世界的感觉及其与其他人感觉的牵连程度。在我看来,这个和其他人感觉的牵连,首先是和时代现实的牵连。无论在什么处境下,诗人都应该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并把这种敏感性转化为诗。这是诗人最重要的职责。
Q5
伯竑桥:站在2024年的节点上去觉察:人们称之为“时代”的混沌物,它坐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革命的门槛上,就要起身进屋了,而一些写作者好像还在前现代的田野里徘徊,连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困惑都没能应对。一场危机还未被摸清楚就要加深了,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老师,您以前对我谈过,“某种程度上,1990年代的诗人是生活在‘垃圾时间’中的,在垃圾时间中怎么写作?这构成了挑战”。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时代对诗人们来说是什么“时间”?不论词语层面还是写作者主体人格层面,汉语诗歌界要如何做好准备去面对即将到来的客观世界的剧变呢?
西 渡:情况也许比你说的更严峻,无论你是否喜欢“时代”,它已经是屋子里的庞然大物了。不过,在我们这里,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几乎是同时到来的,一些写作者还在前现代的田野里徘徊并非不可原谅。我把前现代也理解为当代诗歌的处境之一。
如果说1990年代的时间是垃圾时间,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终场的时间、最后的时间。是诗歌的最后的时间,甚至是人类的最后的时间。AI取代人类不只是一个科幻题材。面对这个最后的时间,诗和诗人应该悲观吗?然而我并不悲观。诗仍然要把最后的时间当作创世的时间。在最后的时间里,诗仍然是一种永远在开始的奇迹。即使我们明天就要告别,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好日子,幸福和闪亮的日子。让终场的哨声见鬼去吧!无论如何,我们仍然要生活。诗不就是对生活的渴望吗?只要我们不丧失对生活的渴望,并忠于我们的生活,诗就不会离我们而去。
诗人的词语并不来自词典,而是来自生活。和所有热爱生活的普通人一样去生活,去经历、去承受命运分配给你的那一份幸福和痛苦,去劳作和创造,去观察和发现,去感受和体验,让你对生活的爱成为诗的源头。无论生活的处境如何,无论在最后的时间里生活面临怎样的挑战,保持感受力的完整、开放,让同情和怜悯永远陪侍左右,永远不要麻痹和冷漠……
Q6
伯竑桥:前些年,您与雷格关于“新诗的大诗人尚未诞生”的对谈仿佛引爆水雷一样触发了听众的关注和焦虑。然而在讨论其他更具体的诗歌问题的时候,圈子内也几乎很难取得共识。那么如果说新诗的一些基本性的、百年来早已讨论过无数次的问题,至今都没有成为领域内的常识,这是为什么?据此,受不少人期待的通常意义上的“大诗人”,在一个解构性的时代还会被确立吗?
西 渡:关键是谁的常识。诗人的常识不同于批评家的常识,也不同于读者的常识。实际上,诗歌并不是常识,也可能诗歌就是反常识的。我们不能指望诗歌的问题以常识的方式解决。一旦某些东西成为常识,在诗人那里,它就成了诗的反面,诗人总是倾向于远离它。诗人不断地离开常识,而读者刻舟求剑地死抱常识,这是共识根本不可能达成的原因。蝉已经蜕壳飞去,读者却守着一堆蝉壳不放。“花落知多少”“床前明月光”是大多数读者的常识,但用这样的常识来反对当代诗歌是一种蒙昧的做法,有时候纯粹是耍无赖。
“大诗人”也没有绝对的标准。用莎士比亚的标准,杜甫是大诗人吗?也可以反过来,用杜甫的标准,莎士比亚是大诗人吗?其实我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解除诗人们的“大师”焦虑。但实际的效果相反,一些诗人似乎更焦虑了。也许没有公认的大诗人正是新诗的一个不凡成就。没有定于一尊,新诗就依然保持了它的开放性和可能性,保持了它的活力。至少现代汉语的好诗远远没有做完,我们的努力仍大有前途。
Q7
伯竑桥:我记得臧棣说过,新诗至今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它 历经百年后作为文体依然存在,并且仍有大量的人在写(大意 如此)。这种说法巧妙且“棒喝”,有它新诗史层面的由来, 听起来很甘甜。大概是我作为年轻人关注的重点会不同,有时候忍不住想:这种甘甜的说法会不会在无意中成为一种文学版本的“不争论”,和“相信下一代人的智慧”?这其中,对新诗合法性的乐观辩护令人安心,同时似乎有对具体困境的遮蔽之虞,您怎么看?
西 渡:臧棣的说法有他的针对性。现代历史上,否定新诗的势力太强大了。大人物们几乎都否定新诗。鲁迅在1936年对斯诺说,“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样,他们实在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钱锺书在1950年对人说,“现代诗”应该叫“绝代诗”,因为1950年以后,再不会有人读这些东西了。毛泽东在1958年说,“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季羡林在21世纪初说,新诗实验是一个失败,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韩寒说现代诗的唯一技巧是回车,责问现代诗和现代诗人怎么还存在。普通读者则把这些名人名言当作常识接受下来,用作攻击新诗的武器。在这样的攻击之下,新诗依然存在,确实可以算作一个成就,可以验证它的生命力。上述种种议论,出自新诗的不同阶段,它们的针对也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只能算作闲话,并不是严肃的讨论。认真辩论起来,其实不值一驳。针对这样的攻击,臧棣的回答是机智的,也可以说是智慧的,显示了诗人在外行面前的骄傲。事实上,经过百年发展,新诗已有足够的当量和能量针对此类闲话为自己辩护,根本无须诗人和批评家插嘴。当然,这样的回答方式不负责解决新诗的具体困境。具体的困境需要在每个诗人的写作中解决。不同的诗人需要面对各自不同的问题,而且每个诗人在不同的阶段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但所有这些具体问题加起来,都不会妨碍新诗已经巍然存在这一事实。
Q8
伯竑桥:在我所感知到的您的诗学体系里,“写作者的心灵”(人格)是一个重要的命题。譬如您谈过左翼写作者在现实中的革命成功后,心灵结构未能更新而复为封建的惋惜;再譬如,您对歌德始终不衰的兴致,对他身上的那种在文学大师里绝无仅有的现实感和平衡感的推重;不仅如此,您对艾青、昌耀、北岛、海子等的人格弱点对自身写作成就的制约也有批评。人格的修炼在诗歌道路上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您认为这种平衡感与现实感是您所朝向的道路吗?
西 渡:最近在回答关于当代诗歌的提问时,我表达了一个观点:现代诗一体于人格。这也是我一贯的看法。诗就是人格的实践和完成。这不止是文如其人。文如其人某种程度上还是修辞的问题。也不止是怎么写就怎么生活的问题。这还是把写和生活看作两件事。我认为,诗就是实践,诗和生活、人生就是一件事,把两者割裂开来,写是写,生活是生活,要么把诗看轻了,要么把生活看轻了,都是不能接受的。我对诗的爱就是对生活的爱,我对生活的爱中也无法排除对诗的爱,没有诗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写作者的人格品质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在我看来,自由是一种综合的品质,它本身就是完整人格的体现。自由人格包括多种因素:不屈从于权力的独立性,思想的自由,爱和悲悯的能力,直面现实的勇气,智慧和坚忍。这些品质都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脱离自由,它们将无法存在。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我认为没有生而自由这一说。自由是一种斗争。自由的道路是窄的。条条道路通向奴役,物质的奴役,思想的奴役,精神的奴役……诗是自由的盟友,失去这个盟友,诗就会从天上坠落深渊。诗歌的很多失败都可以归结为自由的失败。牛汉编《艾青诗选》,只收艾青1941年以前的作品,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值得重视的。不光是艾青,碰到牛汉这样严格的选家,有多少诗人会被“腰斩”?在我看来,从现代过来的诗人,没有例外,都需要牛刀一断,有的则需要“砍头”。很多诗人恐怕连“砍头”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从不知道自由是什么。
我对歌德的现实感和平衡感极为拜服。对我来说,歌德是永远的榜样,其平衡感和现实感是纠正现代文学的极端性和否定主义的良药。歌德是不断成长、永远成长的榜样,也是书写肯定之诗、幸福之诗的榜样,更是自由的榜样。冯至是歌德最虔诚的崇拜者之一,可惜他未能在自由的品质上追随歌德,他也是要被牛汉“腰斩”的诗人。恩格斯对歌德有个批评,说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在我看来,歌德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的天才之中,更表现在恩格斯批评的“渺小”和“庸俗”之中。歌德是精力无穷的天才,在世俗生活中却愿意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人,“谨小慎微”“事事知足”,遵守习俗,这是他的现实感和平衡感的体现,也是他的谦恭和自我抑制的表现,而且这谦恭又如此真诚,并不是伪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在这种谦恭和自抑中,众多天才难免的自大、自私、独断的缺点被克服了。这大概就是伟大诗人和才子的区别。
Q9
伯竑桥:您是重要的诗人,也是相当有分量的诗歌批评家,按您的自述,开始写批评是出于偶然(为推广戈麦的诗而写)。记得您说过,好的诗人天然地就是批评家。在您的内心里和生活中,是怎么调和这两个身份的呢?
西 渡:诗和批评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写诗和做批评依赖 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能力。批评是一个理智的工作,写诗主要依 赖感受力的展开。诗的推进主要依靠直觉、想象和节奏,批评的推进主要依靠逻辑和推理。两者在我这里是分开的。当我做批评工作的时候,我几乎不写诗,甚至在我教诗歌写作的时候,我也没法写诗。教人写诗也是一个理智的工作。两者交错进行的情况也不多。实际上,我花在写诗的时间上是很少的,教学工作之外,我的时间更多花在批评上。当然,两者远远谈不上井水不犯河水。当你从事其中任何一项工作时,都需要另一项工作中养成的能力前来襄助。写诗需要理智的协助,批评也需要感受力、想象力的协助。判断力是两者的交集。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列举了诗人所需要的六种能力,包括观察和描绘的能力、感受力、沉思的能力、想象和幻想的能力、虚构的能力(华兹华斯指虚构人物和场景的能力,不同于一般的想象和幻想)、判断的能力。华兹华斯说,判断力“决定应该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并且在什么程度上把上述几种能力中间的每一种能力加以运用,以致较小的能力不被较大的能力所牺牲,而较大的能力不轻视较小的能力,不攫取比它所应得的更多的东西,而对它本身有害。每种写作的规律和相当优点也是由判断力所决定的”。就是说,判断力是指挥、调节其他诗歌能力的能力。没有判断力,诗歌写作和批评工作都无法进行。判断力的介入使诗人同时成为一个批评家。一个最好的诗人在写的同时进行批评,一个合格的诗人在修改的时候进行批评,只有坏的诗人才不进行批评,因为他不具备判断力。从波德莱尔开始,现代大诗人都是大批评家。兼擅创作和批评已经是现代诗的内在要求。对于批评家来说,判断力是其工作的起点,没有判断力的批评家是没有味觉的厨师或天生失聪的音乐家,没有判断力的批评工作是盲人骑瞎马。这是一种AI式的批评,听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一无所知。
在内心里,我主要把自己看作一个诗人,而不是批评家。因为写是我的出发点,可以说我的批评是从写出发的,但不能反过来说,批评是写的出发点。不过,从事批评工作让我对写的感觉有所不同。如果写是一种表达,批评则主要是一种倾听。它让我关心别人的写作,让我知道其他人、其他声音的存在。它对诗人的自我中心是一种纠正。它使我的写和别人的写相连接。克尔凯郭尔说,耳朵是精神化程度最高的器官。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把“听”解释为“圣之藏于耳者也”。对任何个体来说,听都比说更本源。也可以说,说是源于听的。一个诗人批评家对天才病具有更强的免疫力,大概也源于此吧。
Q10
伯竑桥:越来越多的青年写作者这几年都在读博、进高校,规模之大,好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没有过。在您看来,汉语新诗和学院场域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可能会给未来的汉语诗歌带来什么新变化?
西 渡:诗人读博士、进高校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臧棣、麦芒等是最早的一批,周瓒、姜涛、胡续冬等继之。胡续冬曾化用海子的诗句自嘲说,“我走到了学位的尽头”。从那个时候开始,诗人的学历就普遍高于小说家了。王蒙在1980年代提倡作家学者化,诗人率先于小说家实现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是诗人在谋生方面的劣势。好的小说家养活自己没问题,如果畅销,也可以活得很好。但诗人不行,一个时代最好的诗人也难以靠写诗养活自己。奥登名满天下,也还要靠写评论贴补家用。拉金做图书管理员。勃莱到处朗诵自己的诗。从罗伯特·潘·沃伦到沃尔科特,大批美国诗人在高校靠教书混口饭吃。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名诗人都是专业诗人,在作协领工资。随着作协体制的改革,专业作家的名额越来越少,也轮不到诗人,高校就成了诗人们最后的收容所。
在1980年代,诗人们普遍存在反学院情结,认为诗人是天才的事业,学院的平稳生活足以扼杀诗人的天才。所以,那时候,谁也不愿戴上一顶学院的帽子。现在诗人的学院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学院诗人的自我辩护是,高校生活也是生活,在学校里遇到的人也是三六九等,各种矛盾冲突与社会无异,何况现代诗的写作主要依赖诗人的虚构能力和诗人的内在生活,生活的平静根本不会成为写作的障碍。而且谋生于高校,和诗歌写作上的学院派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也是,生活在高校的中国诗人比混社会的诗人更具有先锋和实验特色,这和美国的新批评学院诗人很不一样。
我大致同意上述辩护,但也不能不承认,学院生活确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学院的经验与院外经验总有差异。学院在社会结构中还是上层建筑的性质,对诗人了解、体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会有遮蔽。依靠智力谋生的方式和单一的书斋生活,难免导致经验单一化。大家都往学院去,又导致经验的趋同。这应该是当前诗歌题材、主题、风格雷同化的一个原因。身体的弃置导致对头脑的过分依赖,诗歌感性退化。上述种种还可能导致已经非常稀有的诗歌读者的流失。对于没有学院体验的读者,对诗歌的学院化有抱怨很正常。这些可能是消极的影响。正面或者中性的影响也有。学历的普遍提高和长久的学术训练导致批评介入写作的程度越来越深,写作的自觉程度越来越高,技艺更讲究,题材上和主题上内向化,语言也偏于文雅,糙嗓门少了。这是就整体的倾向而言。但对于杰出的诗人来诗,这些积极、消极的影响都不足以决定他的写作。无论生活在学院,还是生活在大杂院,抑或是在偏僻的山区,他的心灵总是能和人群、万物乃至宇宙相通。
总体来说,学院生活大致还是一个旁观的位置,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它是艾青的位置,不是穆旦的位置。艾青是抗战的歌手,但是他的歌都是在后方唱的。艾青歌颂战士,但他自己不是战士,他自己也没有直接在一线参与战争,或者参与的程度是有限的,他笔下的战士是想象出来的。穆旦是从战争第一线苦熬过来的,他自己就是战士,他的抗战诗在主题的深度、体验的深刻、感性的饱满上都不是艾青所能及的。穆旦的战争诗,身体是在场的,身体的经历决定了感性的表现。当代诗太相信语言,太依赖语言,以为语言决定一切。这种语言决定论我觉得是非常可疑的。我们说,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身体是决定的关键。身体不仅决定我们的感受,也决定我们的思维,还决定我们的语言。沃尔科特说,要改变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诗人不能仅仅在语言中冒险。所以,我倒是觉得诗人不妨尝试另外的生活,不必一窝蜂都往学院挤。另外,无论你是否在校,在题材和主题上做一些扩大的尝试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还是要让身体活跃起来,参与到时代的实践中,从旁观者转到力行者,从安全的位置转到危险的位置。
作者简介:
西渡,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县。1985-198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期间开始写诗。1990年代以后兼事诗歌批评。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2018年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著有诗集《雪景中的柏拉图》《草之家》《连心锁》《鸟语林》《天使之箭》《钟表匠的记忆》,诗论集《守望与倾听》《灵魂的未来》《壮烈风景》《读诗记》等。

